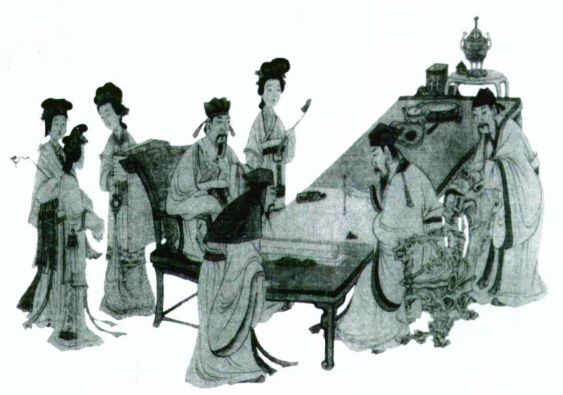精彩推荐
热点关注
专题推荐
-
没有记录!
热点排行
中国古代赐姓赐名制度考论
2014/2/13 11:23:15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摘要:赐姓赐名是古代君主权力染指人名姓氏文化而产生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这一现象在先秦时代主要表现为分封赐姓,而秦汉以降则表现为贵姓嘉名的德赐与恶姓丑名的凶赐两个不同方面。古代君主通过德赐褒奖笼络臣下或利用凶赐打击羞辱犯罪之臣,赐姓赐名因其具有明显的社会政治功能而成为古代君主专制行之有效的统治工具。
一
在中国古代姓氏文化发展史上,姓氏赐予现象的产生,可溯源于距今5000年左右的父系氏族社会。《续文献通考》卷二O七《氏族考》载:“炎帝姓姜,太皞所赐也;黄帝姓姬,炎帝所赐也。尧赐伯夷姓曰姜,赐禹姓曰姒,赐契姓曰子,赐稷姓曰姬,是天子之赐也。”此段材料中涉及的炎帝、太嗥、黄帝、尧、伯夷、禹、契、稷等人物,均是父系社会不同时期或不同区域的部落首领,他们的族姓全由受赐而来,足以证明姓氏赐予在父系时期就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姓氏赐予的产生,是私有制发展的结果,是原始社会末期王权政治需要的产物。父系社会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彻底摧毁了原始公有制度,社会成员因私有财产占有的悬殊加速贫富分化。贫富分化的结果不仅使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消失,而且最终导致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经济剥夺与人身支配,社会形成对立的两大阶级。伴随阶级的出现,早期的国家形态产生,父系社会时期的部落联盟首领由此向国家政治首领即“王”或“天子”转化。王或天子不仅对他的部落臣民握有生杀予夺的惩罚之权,同时也拥有恩宠赏赐的褒奖权利。如同天子把普天之下的有形财富如土地、牲畜、绢帛作为一己之私产任意用于赏赐的情形一样,姓氏赐予,实际上是天子把姓氏作为自己拥有的无形私产而任意支配。其与有形的实物财富赏赐,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统治而对其臣民实施的一种笼络利诱手段。“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1](卷九十五《高俭传》);“赐姓命氏,因彰功德”[2](《氏族典·氏族总部汇考四》)。由此可知,姓氏赐予一开始就是作为褒奖功德的一种政治手段出现的,是王权政治的派生物,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国家政治行为。史载“虞有功,赐姓赢氏”[3](卷二十七《氏族三》);“帝(舜)嘉禹德,赐姓日姒”[2](氏族典卷一《氏族总部汇考一》),此类因功德赏赐而产生的姓氏,均是直接由国家政治行为派生出来的姓氏。
姓氏赐予自肇端之始,其权力就直接操纵掌握在天子(即部落联盟首领)手中,“天子赐姓赐氏”[4](卷二o七《氏族考·总论》);“姓非天子不可以赐”,“姓氏之权出于上”[2](《氏族典卷十八·氏族总部·艺文》)。以后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姓氏赐予直属天子之权的原则一直没有改变。
早期姓氏赐予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以地名作为赐姓姓氏,即所谓“赐土姓”,意即以出生之地或以居住之地的地域名称为赐姓姓氏。《续文献通考》卷二O七《氏族考》云:“赐土姓,言因所生之土而赐之。”如:“居于姚墟者赐以姚,居于赢滨者赐以赢。姬之得赐姬水故也,姜之得赐于姜水故也。故曰因生以赐姓。”[3](卷二十五《氏族一》)这段材料中的居地,实际上就是:“因生以赐姓”的出生地。有关文献对“因生赐姓”有这样明确的解释:“因生以赐姓,谓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赐之姓以显之。”[2](《氏族典卷一·氏族总部汇考一》)如“炎帝之姜,黄帝之姬,始因所生之地而为之姓”[1](卷一二五《张说传》);“舜生妫汭,赐姓曰妫”[4](卷二O七《氏族考·总论》)等等,都是因生赐姓的典型事例。在整个先秦时期,通过赐姓方式,把众多的地域名称先后转化为姓氏名称,是不少新姓氏得以起源创生的重要途径。所谓“人君赐姓赐族,为此姓此族之始祖耳”[2](《氏族典卷十七·氏族总部·总论》)。
早期姓氏赐予还与诸侯分封、建立封国的政治行为密切相关,连同一体。先秦时代,国家政体的主要形态是分封制,王或天子在分封诸侯、建立封国之际,往往同时赐予受封者姓氏,“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2](《氏族典卷十七·氏族总部·总论》)。这里的“天子建德”,意即“立有德以为诸侯”[2](《氏族典卷十七·氏族总部·总论》)。“胙之土而命之氏”,古代学者注疏云:“胙训报也,有德之人必有美报,报之以土,谓封之以国,名以为之氏”[2](《氏族典卷十七·氏族总部·总论》)。
由于封国区域并不一定就是受封者的出生地或居住地,因此,分封赐姓的姓氏选择,既有使用封国国名的情况,也有另赐他姓的现象。《史记·夏纪》:“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禹的后裔受封之后,姓氏名称采用的是封国国名,原来的姒姓便中断不再使用。类似的情况,如“秦之先为赢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营氏、钟离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3](卷二十六《氏族二》)。受封者姓氏变易为封国名称,既有姓氏赐予的方式,但也不排除后代子孙自行改易的情况。不用封国封地之名而对受封者另赐其他姓氏,文献上也不乏记载。比如:“契封于商赐姓子,稷封于邰赐姓姬”[2](《氏族典卷一·氏族总部汇考一》);舜裔孙曰满,在周代“封之于陈,赐姓妫”[1](卷七十一《宰相世系一下》)。此类赐姓虽不采用封国封地之名,但却并没有摆脱以地名为赐姓的惯例习俗。文中的赐姓姬、妫,即是前文提及过的先秦时代重要地名,为姬水和妫讷之简称。
姓氏赐予虽然是先秦时代常见现象,但“非复人人赐也”[2](《氏族典卷十七·氏族总部·艺文》)。史称:“赐族(姓)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始赐之;无大功德,任其兴衰则不赐之”[2](《氏族典卷十七·氏族总部·总论》)。可知,赐姓氏是极为显贵之事,跻身姓氏受赐之列者,均为奴隶主贵族中的上层人物,对一般下层庶民百姓而言,则是完全与他们绝缘的。
二
从秦汉时代起,赐姓氏现象出现了如下一系列新变化。其一,由于各类姓氏创生发展日趋稳固定型,赐姓氏通常不再使用地域名称,先秦时代以地名为赐姓的习俗特征随之消失。其二,建诸侯、立封国在秦汉后不再是经常性、普遍性的国家政治行为,即使有所发生,但受封诸侯多为姓氏高贵的皇族成员,没有必要另赐他姓。因此,赐姓氏与分封制度完全相脱离,封地封国名称不再成为受封者的姓氏名称。其三,秦汉以后,天子姓氏开始被作为国姓凌驾于万姓之上,其神圣独尊的姓氏地位获得社会普遍敬仰与崇拜。用天子姓氏作为赐姓成为秦汉以后姓氏赐予的最重要内容;同时,赐名的现象在秦汉以后也开始普遍出现。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历代封建帝王均把天下视为自己一家一姓之天下,君主的姓氏和国名(即朝代名称)开始连同一体,形成诸如刘汉王朝、李唐王朝、朱明王朝等标示国姓朝代的习惯称谓。用天子国姓于赏赐,荤端于汉高祖刘邦,“高祖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赐姓刘氏”;“娄敬劝高祖都关中……赐姓刘氏”[5](卷十七)。刘邦开此先例,历代君主赐国姓于臣下,便相沿成习。如唐朝国姓为李氏,“赐李氏者,有邴元紘、杜伏威、郝廷玉、宋文通、胡大恩、弘播、郭子和、麻延昌、鲜于叔明、安元谅、张宝臣……皆由立功赐国姓”[4](卷二一二《氏族考·改易姓氏》)。又如明朝,立国之初,“太祖义子数人如李曹国、文忠沐、西平英,都督何文辉、徐司马及元帅文刚、文逊等,皆赐国姓”[4](《氏族考·改易姓氏》)。朱元璋在明初开赐义子国姓之例后,明武宗时期曾出现过“正德七年(1512).赐义子百二十七人国姓”[2](《氏族典》卷三)的豪举。其他如“诏都督江彬、许泰、刘晖、张洪、李琮,指挥焦睿,俱赐国姓”;“都督钱宁、钱安、许国,赐朱姓”[4](卷二一二《氏族考·改易姓氏》)等等,都是明朝赐国姓的典型事例。明末清初著名的爱国将领郑成功,原名郑森,字大木,因深得南明政权隆武帝器重,“因赐姓朱,改名成功”[6](233页)。
考察历代国姓赐予,赐姓原因各有差别,受赐途径具有多元化特征。如“王莽时,刘嘉以献符瑞,封扶美侯,赐姓王氏”[4](卷二一二《氏族考·改易姓氏》)。又如丙粲,“唐左监门大将军,应国公,高祖与之有旧……赐姓李氏”[1](卷七十二《宰相世系二上》),这是因为与李唐开国皇帝李渊是故友旧交,由此获得国姓赏赐。再如“武后改推为周,赐豫王旦、庐陵王、故太子贤子光顺等与契苾明妻及母临洮公主皆姓武氏。又以史务滋为纳言,宗楚客为检校内史,傅游艺为鸾台内史平章事,并赐姓武氏”[4](卷二一二《氏族考·改易姓氏》)。武则天篡唐建立武周政权以后,通过公开的姓氏赐予把部分李唐宗室成员及一批文
武大臣的姓氏改为武姓,武氏的国姓权威地位便由此确立起来,这是宫廷政治斗争引起的赐国姓现象。另如元朝时,“贺惟一,顺帝时赐蒙古氏名太平。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台端非国姓不授,太平固辞,特诏赐姓”[4](卷二一二《氏族考·改易姓氏》)。元代的情况比较特殊,这里的国姓是指蒙古人的姓氏,由于元政府规定御史台即“台端”的官员非蒙古国姓不授,因此,汉族官员贺惟一获“特诏赐姓”的恩宠,是出于朝廷人才选拔使用的政治需要。
古代受赐国姓最常见、最普遍的途径,是军功赐国姓。从有关文献的记载情况看,那些征战沙场,为君主出生入死且战功显赫者或为国捐躯者,其本人及家族最有可能获得赐国姓的恩宠。“秦贞父能死难,魏武赐姓曹氏”;“杨义臣本姓尉迟,文帝因其父战死,赐姓杨,编之属籍”[7](卷二十八);唐将“光进、光颜皆以战功至大官,赐姓李氏”[1](卷二一七《回鹘传下》)。对封建君主而言,“其有倚为腹心者,则赐以皇族之姓”[7](卷二十八)。显然,君主们一般不会轻易把自己的姓氏赐予臣下,只有认定或证明其确实是能为自己拼死效命的腹心爪牙,才有可能给予其这一政治殊荣。
在中国古代,以军功赐国姓最典型、最规范化、制度化的,是金朝的赐国姓制度。史载女真人在黄河流域建立金朝政权以后,一方面因与宋朝长期对峙而战争连绵不断;另一方面,又因北方的蒙古势力日益崛起而不断受到来自蒙古人向外扩张的强大武力威胁。金统治者为此制订了包括国姓赐予在内的种种措施,以适应军事战争的需要。史称金朝“赐姓有格……计功而得国姓”[8](卷一0一《完颜佐传》)。这里的“计功”,是指完全量化的军功。《续文献通考》卷二一二《氏族考》详细记载了女真统治者为“计功”而设定的量化指标,“金制,赐国姓者:凡以千人败敌三千者,赐及缌麻以上;败两千人以上者,赐及大功以上;败千人以上,赐及其身”。由此可知,如果女真军人所立军功达到朝廷量化指标,不仅其本人,甚至包括其“缌麻”、“大功”范围之内的亲属成员,均可一并享受国姓赐予的恩宠。金朝军人通过效命疆场而获赐国姓的现象相当普遍,“其功多或力大可恃以为援者,则竟赐以皇族之姓,如郭仲元、郭阿憐、李震、梁佐、李咬住、国用安、张甫等,皆赐姓完颜氏”[7](卷二十八)。这是由金朝政权处于极其严峻的军事险恶环境这一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由于在古代赐姓现象中,国姓为姓氏赐予的最高规格,因此,凡因功受赐姓氏者,都希望获赐国姓而非其他姓氏。《续文献通考》卷二一二《氏族考·改易姓氏》条载:“西京都统程琢有功,诏赐琢姓夹谷氏。琢请曰:‘前代皆赐国姓,不系他族,如蒙更赐,荣莫大焉。’诏更赐完颜氏。”夹谷氏为女真大姓,但受赐者对这一姓氏获赐并不满足,在其本人的请求之下,朝廷收回已经颁发的赐姓诏令,另发诏书改赐国姓完颜氏。这反映出天子国姓在姓氏受赐者心目中始终具有其他姓氏不可替代的神圣至尊地位。
然而,秦汉以来的皇帝赐姓,却并不仅仅限于国姓的赐予,国姓之外,其他姓氏的选择使用,也是皇帝赐姓中屡见不鲜的现象。如“金曰磾,本匈奴休屠王之子,降汉,武帝以休屠用金人祭天,赐姓金氏”(卷二一二《氏族考·改易姓氏》)。这里的赐姓金,是因为匈奴把金作为祭天之物,有以金为贵之意。又如“贺若氏,代居玄朔,无姓。随魏南迁,北俗以忠贞为贺若,因赐姓氏焉”(卷二一二《氏族考·改易姓氏》)。这里的赐姓贺若,是取其“忠贞”的美好寓意。其他如员半千,“其先彭城刘氏,以忠烈自比伍员,因赐姓员”[l](卷一一二《员半千传》);桓彦范,“加特进,封扶郡王,赐姓韦”[1](卷一二0《桓彦范传》)。赐姓员,是满足受赐者对伍员(伍子胥)的仰慕之情;赐姓韦,是因为韦氏是当时极为显贵的姓氏①。凡此一类非国姓的姓氏赐予,大多选用吉祥、高贵或寓意美好的姓氏,虽比不上赐国姓尊崇,但由于是以皇帝的名义赏赐姓氏,对受赐者而言,始终不失为令时人羡慕不已的一种特殊政治荣耀。
一
在中国古代姓氏文化发展史上,姓氏赐予现象的产生,可溯源于距今5000年左右的父系氏族社会。《续文献通考》卷二O七《氏族考》载:“炎帝姓姜,太皞所赐也;黄帝姓姬,炎帝所赐也。尧赐伯夷姓曰姜,赐禹姓曰姒,赐契姓曰子,赐稷姓曰姬,是天子之赐也。”此段材料中涉及的炎帝、太嗥、黄帝、尧、伯夷、禹、契、稷等人物,均是父系社会不同时期或不同区域的部落首领,他们的族姓全由受赐而来,足以证明姓氏赐予在父系时期就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姓氏赐予的产生,是私有制发展的结果,是原始社会末期王权政治需要的产物。父系社会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彻底摧毁了原始公有制度,社会成员因私有财产占有的悬殊加速贫富分化。贫富分化的结果不仅使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消失,而且最终导致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经济剥夺与人身支配,社会形成对立的两大阶级。伴随阶级的出现,早期的国家形态产生,父系社会时期的部落联盟首领由此向国家政治首领即“王”或“天子”转化。王或天子不仅对他的部落臣民握有生杀予夺的惩罚之权,同时也拥有恩宠赏赐的褒奖权利。如同天子把普天之下的有形财富如土地、牲畜、绢帛作为一己之私产任意用于赏赐的情形一样,姓氏赐予,实际上是天子把姓氏作为自己拥有的无形私产而任意支配。其与有形的实物财富赏赐,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统治而对其臣民实施的一种笼络利诱手段。“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1](卷九十五《高俭传》);“赐姓命氏,因彰功德”[2](《氏族典·氏族总部汇考四》)。由此可知,姓氏赐予一开始就是作为褒奖功德的一种政治手段出现的,是王权政治的派生物,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国家政治行为。史载“虞有功,赐姓赢氏”[3](卷二十七《氏族三》);“帝(舜)嘉禹德,赐姓日姒”[2](氏族典卷一《氏族总部汇考一》),此类因功德赏赐而产生的姓氏,均是直接由国家政治行为派生出来的姓氏。
姓氏赐予自肇端之始,其权力就直接操纵掌握在天子(即部落联盟首领)手中,“天子赐姓赐氏”[4](卷二o七《氏族考·总论》);“姓非天子不可以赐”,“姓氏之权出于上”[2](《氏族典卷十八·氏族总部·艺文》)。以后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姓氏赐予直属天子之权的原则一直没有改变。
早期姓氏赐予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以地名作为赐姓姓氏,即所谓“赐土姓”,意即以出生之地或以居住之地的地域名称为赐姓姓氏。《续文献通考》卷二O七《氏族考》云:“赐土姓,言因所生之土而赐之。”如:“居于姚墟者赐以姚,居于赢滨者赐以赢。姬之得赐姬水故也,姜之得赐于姜水故也。故曰因生以赐姓。”[3](卷二十五《氏族一》)这段材料中的居地,实际上就是:“因生以赐姓”的出生地。有关文献对“因生赐姓”有这样明确的解释:“因生以赐姓,谓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赐之姓以显之。”[2](《氏族典卷一·氏族总部汇考一》)如“炎帝之姜,黄帝之姬,始因所生之地而为之姓”[1](卷一二五《张说传》);“舜生妫汭,赐姓曰妫”[4](卷二O七《氏族考·总论》)等等,都是因生赐姓的典型事例。在整个先秦时期,通过赐姓方式,把众多的地域名称先后转化为姓氏名称,是不少新姓氏得以起源创生的重要途径。所谓“人君赐姓赐族,为此姓此族之始祖耳”[2](《氏族典卷十七·氏族总部·总论》)。
早期姓氏赐予还与诸侯分封、建立封国的政治行为密切相关,连同一体。先秦时代,国家政体的主要形态是分封制,王或天子在分封诸侯、建立封国之际,往往同时赐予受封者姓氏,“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2](《氏族典卷十七·氏族总部·总论》)。这里的“天子建德”,意即“立有德以为诸侯”[2](《氏族典卷十七·氏族总部·总论》)。“胙之土而命之氏”,古代学者注疏云:“胙训报也,有德之人必有美报,报之以土,谓封之以国,名以为之氏”[2](《氏族典卷十七·氏族总部·总论》)。
由于封国区域并不一定就是受封者的出生地或居住地,因此,分封赐姓的姓氏选择,既有使用封国国名的情况,也有另赐他姓的现象。《史记·夏纪》:“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禹的后裔受封之后,姓氏名称采用的是封国国名,原来的姒姓便中断不再使用。类似的情况,如“秦之先为赢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营氏、钟离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3](卷二十六《氏族二》)。受封者姓氏变易为封国名称,既有姓氏赐予的方式,但也不排除后代子孙自行改易的情况。不用封国封地之名而对受封者另赐其他姓氏,文献上也不乏记载。比如:“契封于商赐姓子,稷封于邰赐姓姬”[2](《氏族典卷一·氏族总部汇考一》);舜裔孙曰满,在周代“封之于陈,赐姓妫”[1](卷七十一《宰相世系一下》)。此类赐姓虽不采用封国封地之名,但却并没有摆脱以地名为赐姓的惯例习俗。文中的赐姓姬、妫,即是前文提及过的先秦时代重要地名,为姬水和妫讷之简称。
姓氏赐予虽然是先秦时代常见现象,但“非复人人赐也”[2](《氏族典卷十七·氏族总部·艺文》)。史称:“赐族(姓)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始赐之;无大功德,任其兴衰则不赐之”[2](《氏族典卷十七·氏族总部·总论》)。可知,赐姓氏是极为显贵之事,跻身姓氏受赐之列者,均为奴隶主贵族中的上层人物,对一般下层庶民百姓而言,则是完全与他们绝缘的。
二
从秦汉时代起,赐姓氏现象出现了如下一系列新变化。其一,由于各类姓氏创生发展日趋稳固定型,赐姓氏通常不再使用地域名称,先秦时代以地名为赐姓的习俗特征随之消失。其二,建诸侯、立封国在秦汉后不再是经常性、普遍性的国家政治行为,即使有所发生,但受封诸侯多为姓氏高贵的皇族成员,没有必要另赐他姓。因此,赐姓氏与分封制度完全相脱离,封地封国名称不再成为受封者的姓氏名称。其三,秦汉以后,天子姓氏开始被作为国姓凌驾于万姓之上,其神圣独尊的姓氏地位获得社会普遍敬仰与崇拜。用天子姓氏作为赐姓成为秦汉以后姓氏赐予的最重要内容;同时,赐名的现象在秦汉以后也开始普遍出现。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历代封建帝王均把天下视为自己一家一姓之天下,君主的姓氏和国名(即朝代名称)开始连同一体,形成诸如刘汉王朝、李唐王朝、朱明王朝等标示国姓朝代的习惯称谓。用天子国姓于赏赐,荤端于汉高祖刘邦,“高祖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赐姓刘氏”;“娄敬劝高祖都关中……赐姓刘氏”[5](卷十七)。刘邦开此先例,历代君主赐国姓于臣下,便相沿成习。如唐朝国姓为李氏,“赐李氏者,有邴元紘、杜伏威、郝廷玉、宋文通、胡大恩、弘播、郭子和、麻延昌、鲜于叔明、安元谅、张宝臣……皆由立功赐国姓”[4](卷二一二《氏族考·改易姓氏》)。又如明朝,立国之初,“太祖义子数人如李曹国、文忠沐、西平英,都督何文辉、徐司马及元帅文刚、文逊等,皆赐国姓”[4](《氏族考·改易姓氏》)。朱元璋在明初开赐义子国姓之例后,明武宗时期曾出现过“正德七年(1512).赐义子百二十七人国姓”[2](《氏族典》卷三)的豪举。其他如“诏都督江彬、许泰、刘晖、张洪、李琮,指挥焦睿,俱赐国姓”;“都督钱宁、钱安、许国,赐朱姓”[4](卷二一二《氏族考·改易姓氏》)等等,都是明朝赐国姓的典型事例。明末清初著名的爱国将领郑成功,原名郑森,字大木,因深得南明政权隆武帝器重,“因赐姓朱,改名成功”[6](233页)。
考察历代国姓赐予,赐姓原因各有差别,受赐途径具有多元化特征。如“王莽时,刘嘉以献符瑞,封扶美侯,赐姓王氏”[4](卷二一二《氏族考·改易姓氏》)。又如丙粲,“唐左监门大将军,应国公,高祖与之有旧……赐姓李氏”[1](卷七十二《宰相世系二上》),这是因为与李唐开国皇帝李渊是故友旧交,由此获得国姓赏赐。再如“武后改推为周,赐豫王旦、庐陵王、故太子贤子光顺等与契苾明妻及母临洮公主皆姓武氏。又以史务滋为纳言,宗楚客为检校内史,傅游艺为鸾台内史平章事,并赐姓武氏”[4](卷二一二《氏族考·改易姓氏》)。武则天篡唐建立武周政权以后,通过公开的姓氏赐予把部分李唐宗室成员及一批文
武大臣的姓氏改为武姓,武氏的国姓权威地位便由此确立起来,这是宫廷政治斗争引起的赐国姓现象。另如元朝时,“贺惟一,顺帝时赐蒙古氏名太平。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台端非国姓不授,太平固辞,特诏赐姓”[4](卷二一二《氏族考·改易姓氏》)。元代的情况比较特殊,这里的国姓是指蒙古人的姓氏,由于元政府规定御史台即“台端”的官员非蒙古国姓不授,因此,汉族官员贺惟一获“特诏赐姓”的恩宠,是出于朝廷人才选拔使用的政治需要。
古代受赐国姓最常见、最普遍的途径,是军功赐国姓。从有关文献的记载情况看,那些征战沙场,为君主出生入死且战功显赫者或为国捐躯者,其本人及家族最有可能获得赐国姓的恩宠。“秦贞父能死难,魏武赐姓曹氏”;“杨义臣本姓尉迟,文帝因其父战死,赐姓杨,编之属籍”[7](卷二十八);唐将“光进、光颜皆以战功至大官,赐姓李氏”[1](卷二一七《回鹘传下》)。对封建君主而言,“其有倚为腹心者,则赐以皇族之姓”[7](卷二十八)。显然,君主们一般不会轻易把自己的姓氏赐予臣下,只有认定或证明其确实是能为自己拼死效命的腹心爪牙,才有可能给予其这一政治殊荣。
在中国古代,以军功赐国姓最典型、最规范化、制度化的,是金朝的赐国姓制度。史载女真人在黄河流域建立金朝政权以后,一方面因与宋朝长期对峙而战争连绵不断;另一方面,又因北方的蒙古势力日益崛起而不断受到来自蒙古人向外扩张的强大武力威胁。金统治者为此制订了包括国姓赐予在内的种种措施,以适应军事战争的需要。史称金朝“赐姓有格……计功而得国姓”[8](卷一0一《完颜佐传》)。这里的“计功”,是指完全量化的军功。《续文献通考》卷二一二《氏族考》详细记载了女真统治者为“计功”而设定的量化指标,“金制,赐国姓者:凡以千人败敌三千者,赐及缌麻以上;败两千人以上者,赐及大功以上;败千人以上,赐及其身”。由此可知,如果女真军人所立军功达到朝廷量化指标,不仅其本人,甚至包括其“缌麻”、“大功”范围之内的亲属成员,均可一并享受国姓赐予的恩宠。金朝军人通过效命疆场而获赐国姓的现象相当普遍,“其功多或力大可恃以为援者,则竟赐以皇族之姓,如郭仲元、郭阿憐、李震、梁佐、李咬住、国用安、张甫等,皆赐姓完颜氏”[7](卷二十八)。这是由金朝政权处于极其严峻的军事险恶环境这一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由于在古代赐姓现象中,国姓为姓氏赐予的最高规格,因此,凡因功受赐姓氏者,都希望获赐国姓而非其他姓氏。《续文献通考》卷二一二《氏族考·改易姓氏》条载:“西京都统程琢有功,诏赐琢姓夹谷氏。琢请曰:‘前代皆赐国姓,不系他族,如蒙更赐,荣莫大焉。’诏更赐完颜氏。”夹谷氏为女真大姓,但受赐者对这一姓氏获赐并不满足,在其本人的请求之下,朝廷收回已经颁发的赐姓诏令,另发诏书改赐国姓完颜氏。这反映出天子国姓在姓氏受赐者心目中始终具有其他姓氏不可替代的神圣至尊地位。
然而,秦汉以来的皇帝赐姓,却并不仅仅限于国姓的赐予,国姓之外,其他姓氏的选择使用,也是皇帝赐姓中屡见不鲜的现象。如“金曰磾,本匈奴休屠王之子,降汉,武帝以休屠用金人祭天,赐姓金氏”(卷二一二《氏族考·改易姓氏》)。这里的赐姓金,是因为匈奴把金作为祭天之物,有以金为贵之意。又如“贺若氏,代居玄朔,无姓。随魏南迁,北俗以忠贞为贺若,因赐姓氏焉”(卷二一二《氏族考·改易姓氏》)。这里的赐姓贺若,是取其“忠贞”的美好寓意。其他如员半千,“其先彭城刘氏,以忠烈自比伍员,因赐姓员”[l](卷一一二《员半千传》);桓彦范,“加特进,封扶郡王,赐姓韦”[1](卷一二0《桓彦范传》)。赐姓员,是满足受赐者对伍员(伍子胥)的仰慕之情;赐姓韦,是因为韦氏是当时极为显贵的姓氏①。凡此一类非国姓的姓氏赐予,大多选用吉祥、高贵或寓意美好的姓氏,虽比不上赐国姓尊崇,但由于是以皇帝的名义赏赐姓氏,对受赐者而言,始终不失为令时人羡慕不已的一种特殊政治荣耀。
责任编辑:M005文章来源:印象河南网
相关信息
- ·战国私玺中所见古代复姓及源流考
- ·元明蒙汉间赐名赐姓初探
- ·元朝汉族及内迁各民族的姓氏来源与变化
- ·由姓氏制度的发展看两周宗法制的兴衰
- ·演变中的中国姓氏
- ·姓氏中的文化现象解读
- ·姓氏文化与古代法律
- ·姓氏合流论略
- ·姓名文化的活化石
- ·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 ·西魏北周时代胡姓再行与胡汉体制
- ·我国历史上的姓氏变化与民族关系
-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汉化
- ·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
- ·汉语姓名中的文化内涵小议
- ·汉语姓名与汉民族文化心理特征
- ·汉语姓名地名系统的文化透视
- ·从文化角度论中西姓名的内涵
- ·中国姓氏的来源
- ·古人的赐姓现象
- ·复姓里的历史知识
- ·复姓的来历
- ·从汉族人的姓名透视中国传统文化
- ·从“百姓”看中国古代的姓氏制度
- ·避忌改姓现象述略
- ·春秋战国时代的姓氏制度
- ·“同姓不婚”的实质
- ·《礼记》之正名与中国姓氏文化之关系
- ·姓氏趣闻:有趣的十七个姓氏组合
- ·三大姓追源:古高丽国君也是姓王
著名人物
没有记录!
精彩展示
没有记录!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