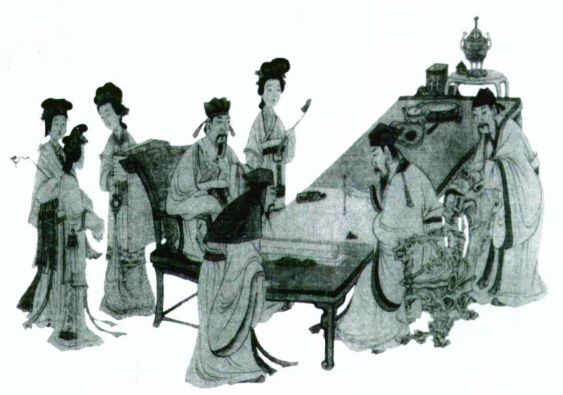精彩推荐
热点关注
专题推荐
-
没有记录!
热点排行
“同姓不婚”的实质
2014/1/4 17:32:19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摘要:“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常被理解为中国古人在优生学上的认识与发现,这一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古代的这一婚姻戒条是远古婚俗的遗留,是原始人群在生存压力下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结果。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写到晋公子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国大夫叔詹谈到重耳的不同常人之处,其一为“男女同性,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国语·晋语四》也写到这件事,其中引人注目的“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一句话写作‘同姓不婚,恶不殖也。’这是两句容易引起虚幻民族自豪感的话,不少学者由此认为,中国古人已经在优生学意义上认识到了近亲结婚对生育的危害。如袁庭栋《占人称谓漫谈》中就说道:“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从实践中总结出近亲不宜通婚的优生学的道理,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国语·晋语四》:‘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利用‘同姓不婚’这一优生学原理来保证后代的正常蕃衍,在古代是长期严格执行的。”[1]
实际上“同姓不婚”并不是对生育问题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同姓不婚”所禁止的通婚范围远远超出优生学上的禁婚范围。优生学只认为直系血亲以及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不利于后代的健康,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对近亲结婚的限制也只在这个范围之内。而中国占代的‘同姓不婚”观念是:只要同姓,则“百世而婚姻不通。”重耳父母的同姓而婚在当时是违背礼制的,由于资料原因,我们无从得知晋献公的这一婚姻是否受到了时人的谴责,而《论语·述而》一段话能让我们看到当时对同姓而婚的反应。鲁昭公娶了吴国公室的女子,吴国与鲁国同为姬姓,同为周朝占公直父的后代,吴国第一代君主是占公的儿子泰伯,鲁国第一代君主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旦,所以陈司败便愤愤地指责鲁昭公道:“君而知礼,敦不知礼。”鲁昭公也心知违礼,不敢按照当时命名夫人的惯例,称她为“吴姬”或“孟姬”,而称之为“吴孟子”。从泰伯到吴孟子,从周公旦到鲁昭公,时间已经过了五六百年,近二十代了,他们的婚姻仍在禁止范围之内,这便不是优生学上的认识了,而是一种非理性习俗或戒条。
另一方面,“同姓不婚”的禁婚范围又遗漏了优生学上的一个重要禁婚领域。中国古代虽泛泛地禁止同姓间的婚姻,却一直不禁止血缘更加亲近的表亲间的婚姻,相反却对表亲间的婚姻津津乐道并积极实行。
刘向《列女传·仁智传·晋羊叔姬》中叔向想娶“美而有色”的夏姬之女,叔向的母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就说:“吾母之族,贵而无庶。吾惩舅氏矣。”母族虽然高贵却生育无多,叔向这样说,不知是他真正认识到了与母族结婚往往“无庶”的规律,还是只感到自己母亲一族生育不蕃,或许仅仅为娶夏姬之女找一漂亮理由,但无论如何,叔向的话在优生学方面还是极有提示性,但这句话历时两千多年一直未能引起极为重视子嗣的中国人的警觉,让人觉得我们的祖先对优生学的问题似乎并不敏感。换一个角度看,叔姬的“不欲娶其族”马上被叔向理解为母亲倾向于娶母族,其中也能透露出叔向的时代娶母族表亲是通常的做法,至少可以说是叔姬平素的愿望。
汉代皇室也是积极实行表亲婚姻的范例。据《史记·外戚世家》及《汉书·外戚传》中记载,仅西汉时期就有惠、景、武、成、哀五位皇帝立其表亲为皇后。吕太后时,“欲为重亲”,便为惠帝娶鲁元公主的女儿(惠帝的甥女)为皇后,这就是张皇后;哀帝的母亲傅太后又是“欲为重亲”,娶从弟的女儿(哀帝的表姊妹)作哀帝的皇后。“欲为重亲”相当于近代的“亲上加亲”,这说明汉皇室的表亲婚姻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一种自觉行为。更值得一提的是惠、景、武等帝的表亲皇后皆无子,却没有引起汉皇室的注意改变这种近亲婚姻,而是继续为成、哀二帝“亲上加亲”,他们当然也没能避开无子或有子而“失之”的结局。如果“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从实践中总结出了近亲不宜通婚的优生学道理”,为什么汉皇室在几代乏嗣的危险情况下,还频频作出这种不利于优生的举动呢?
即使是在春秋时代,时人指出的“男女同姓”的危害,也并非只有“其生不藩”一种。《国语·晋语四》:“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这里说“同姓相及”是“黩敬”,“黩敬”就会由“怨”生“灾”进而“灭姓”。不难看出,这里不是从生殖的危害来否定“同姓而婚”,而是从部族的安定来谈论问题的,并且同姓相及与其可怕的后果间的联系是神秘的,决不是对同姓结婚导致婚姻问题的理性认识。
《左传·昭公元年》有郑国大夫子产批评晋侯的一段话:“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参考一下孔颖达《正义》:“此侨重述不及同姓之意。言内官若娶同性则夫妇所以生疾,性命不得殖长。何者?以其同姓相与先美。今既为夫妻,又相宠爱,美之至极,在先尽矣。乃相厌患而生疾病,非直美极恶生,疾病而已;又美极骄宠,更生妒害也。”原来“其生不殖”不是他们所生的孩子的“不殖”,而是同姓通婚的夫妇的“不殖”,“所以生疾,性命不得殖长”。而他们“相生疾”的原因是:同姓的人本来就相互亲近,成了夫妇又会互相宠爱,两美合起来,亲近程度就达到了极点,物极必反,两人就会转而相互讨厌,也就是像《国语·晋语四》所说的“生怨”,其结果就是“更生妒害”,这样的观点便与“优生学”更不搭界了。
还有一则史料值得我们注意。《左传·隐公八年》: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辛亥,以妫氏归。甲寅,入于郑。陈鍼子送女。先配而后祖。鍼子日:“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诬其祖便不能生育,如果我们联系《国语·晋语四》中的“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一句话,似乎已经看出,古人所谓“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是从亵渎祖先的角度来谈的。同姓而婚,本身是对祖先的不敬,所以“其生不蕃”;异姓相婚本无黩敬的问题,但不守礼制而“诬其祖”,同样也会不育。可见古人认为“其生不蕃”的本质原因不是同不同姓,而是敬与不敬。
类似中国古代“同姓不婚”的婚姻制度或婚姻习俗,在世界各个民族的原始时期都存在过。十九世纪以来,现代人类学家一般称这种习俗为“氏族外婚制”。虽然“氏族”与“姓”并不完全一致,“姓”在范围上往往要大于“氏族”,但它们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血缘区分的社会集团。“氏族内禁止通婚”与“同姓不婚”都是禁止同一社会集团内部的婚姻,它们有着共同的本质。我们可以就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讨论的几个氏族来看看这种习俗实行的普遍性:易洛魁人的氏族规定“氏族的任何成员都不得在氏族内部通婚”[2](第96页),古希腊人的氏族也“禁止氏族内部通婚”[2](第117页),古罗马人的氏族也是“氏族内部不得通婚”。“在名字保存到今天的大量罗马人夫妇中,没有一对夫妇的氏族名称是相同的。”[2](第8项)在此我们不再罗列其他人类学家的类似的发现,因为这一点今天已近乎常识。由此我们说,禁止族内通婚、实行族外婚制是原始时期就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共识,人类在野蛮时期甚至朦昧时期就认识到了近亲不宜结婚的优生学道理显然是荒谬的。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观念来源于原始时期的婚姻禁忌,“其生不蕃”不是理性的思维成果,而是非理性的宗教惩戒甚或是巫术咒语。处于朦昧、野蛮时期的原始人群,不可能用某种理论来指导建立世间制度,他们的制度常常是迫于生存的压力而制定出来的,然后再用宗教的或巫术的信条来论证这一制度的神圣性、不可触犯性,亦使制度稳固下来,保障部族的生存。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其生不蕃”而禁止“男女同性”,而是因为要禁止“男女同姓”才警告说“其生不蕃”。
摩尔根在他的人类学巨著《古代社会》中曾经指出:战争是原始人群间的常态。而解除战争,部族安定、安全地生活的最好方法就是与其他部族结为联盟、化敌为友,在缺乏更多交往方式的原始时代,通婚可能是仅有的结盟方式。人类学家泰勒有一经典的概括:“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许多次,野人部落大概就面临着二者必须择一的选择:要么到另一个部落里去娶个老婆,要么为另一个部落所杀死。”[3] (第42页)通婚成了安全的唯一选择。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的《家庭史》中也有一段更为细致深刻的论述:“如果每一个小的生物性单位都不愿过贫困的生活,不愿心怀恐惧,不愿遭到毗邻而居的其他生物单位的仇恨和敌视,它就必需放弃闭关自守;它必须牺牲自己的特性和连续性,向联姻的各种作法开放门户。~而要保护自己不受外人、甚至敌人侵害,最简单也最可靠的办法,便是通过联姻将这些人变成同盟。”[3](第七页)这段话解释了原始氏族内部禁止通婚这一制度形成的深刻原因:生存安全。祖先在生存的危机中已看到了异姓通婚的重要作用,《语·晋语四》谈到:“故异德合姓,同德合义。义以导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迁,乃能摄固,保其土房。”“异姓则异德”的说法虽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而“异德合姓”的作用却是非常清晰的:“乃能摄同,保其土房。”
传说时代的姬、姜二姓,即黄帝、炎帝二族关系的发展变化,或许能隐约反映出“通婚”在不同族姓间的聚合作用。黄(姬姓)、炎(姜姓)二族本是战争不断的敌对氏族,先秦典籍多有记载。①而到了商朝末年,姜姓成了姬姓翦商的最重要的协助者。同时史书也记载了姬、姜二姓的时代通婚的事实,二姓由敌对转为盟友,互通婚姻起了根本的作用,这一效果是同姓内部同婚所不可能取得的。
通过婚姻来争取联盟或改善关系,在这之后仍是史不绝书的:“(周)襄王欲伐郑,故取翟女为后,与翟共伐郑。”[4]各诸侯国闻也常常通过联姻获得外援增强力量。这种做法如此普遍以致连作为筹码的女子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许穆夫人就曾说:“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国也。”[5]到汉代以至唐代,以通婚的方式与周边民族结盟友好,赢得和平,仍是时常采取的方法。
氏族外婚制或中国古代的姓氏外婚制,其社会作用和历史意义虽然如此巨大,但它并不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要求,而是超越个体的社会要求。要保证氏族外婚制或姓氏外婚制的真正实行,就需要建立相应的宗教戒律,借助神灵的力量来震慑人们违禁的冲动。人类学家在这方面也有丰富的例证,如菲律宾的帕拉望人认为,近亲结婚会引起当事双方的死亡(这与《左传·昭公元年》子产的话是很相似的),也会引起整个部族大雨大热,颗粒无收。[3](第54页)我们原始时期的祖先肯定也经历了这样的阶段,虽然没有文字时代的情况已经杳然无考了,但我们从以上所引的春秋时期的文献中仍能看到“同姓不婚”与宗族生存间的深刻联系,仍能看到这一戒律中的原始宗教色彩。
这一发源于原始时代的婚姻戒律深深地影响了后代的社会生活,“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6]的信条周人俨然纳入礼文,“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警戒也不时回响在礼崩乐坏的混乱时代。秦汉至唐,虽也存在过不禁同姓为婚的短暂时期,如汉末、两晋,战祸连年,晋武帝曾允许同姓通婚。再如南北朝时期,由于强调门第,士族间的通婚范围越来越窄,甚至出现了不少血缘异辈婚。但总的说来,禁止同姓为婚一直十分严格。《唐律》载:“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三年”。《明律》载:“凡同姓为婚者,杖六十,离异。”制裁还是非常严厉的。而且直到今日,台湾以及南洋的华人世界中,还严格遵守“同姓不婚”的戒律。甚至一些异姓联宗的宗族内也明确规定不许通婚。如台北市曾氏宗亲会会讯第四期登载之《福建省海澄县新安乡邱姓与温陵龙山曾姓同宗渊源考》一文,在论证了邱、曾两姓同宗之后,明确提出:凡属海澄新安邱姓子孙,现均与普姓不通婚姻。又如台湾的朱、庄二姓也是异姓联宗,庄氏子孙庄安顺1968年撰《朱庄严三姓渊源》,云:朱、庄不通婚姻,以示同气连枝之也。后代的这些现象中,包括《唐律》、《明律》以刑法维护“同姓不婚”的举动中,优生学的意味是完全不存在的,而更多的是用“同姓不婚”表示对祖先的礼敬,表示同姓间的密切关系。
追根溯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同姓不婚”是处在原始时期祖先在生存压力下作出的社会意义上的选择,而非生殖意义上的选择。如果说这一选择起到了改良人种的作用,那也是无心插柳显现的客观效果,并非有意为之。
参考文献:
[1]袁庭栋.古人称谓漫谈[M].北京:中华书局,199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法]安德烈·比尔基埃等.家庭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8.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张涛.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6]礼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①《太平御览》七九引《归藏》:“昔黄神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日:‘果哉而有咎。…《吕氏春秋·荡兵>:。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淮南子·兵略>:“炎帝为火灾,故黄帝禽之。”《大戴礼·五帝德》:“黄帝教熊、罴、貔、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史记·五帝本纪》:“教熊罴貔貅疆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作者简介:张德苏(1965-),男,山东德州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责任编辑:M005文章来源:印象河南网
下一条:春秋战国时代的姓氏制度上一条:《礼记》之正名与中国姓氏文化之关系
相关信息
著名人物
没有记录!
精彩展示
没有记录!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