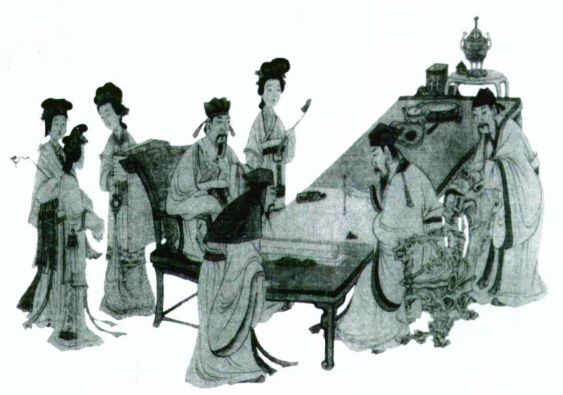精彩推荐
热点关注
专题推荐
-
没有记录!
热点排行
姓氏合流论略
2014/2/11 9:22:10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摘 要:春秋战国之际的姓氏合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为姓氏结构的变化,即姓氏结构由原来的多级制(姓、氏两级或者姓、大宗氏、小宗氏三级)转变为只有变化以后的新姓一级;其二为姓氏应用规则的变化,即在新姓氏制度下,无论男子、女子,其个人的称谓都以“新姓+名”的形式出现,不再有男女两性在姓氏应用规则上的区分。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几乎所有社会制度都在此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此之时,姓氏制度也不能再守其故常,它的变化也方方面面地显现出来。对于这个问题,阎晓君先生《论姓氏合一》一文中曾有过一定的论述,①笔者于深受启发的同时,感到对此问题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和必要。对姓氏合流的具体过程仍需详细地考索,故而不揣浅陋撰成此文,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姓氏结构的变化
姓氏结构的变化是血缘组织结构形式变化的结果。在春秋战国之际,当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进步促使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多级形态,即氏族之下有家族、家族之下可能还有更小的家族的形态,向单级的、以个体家庭为主体的形态转变时,姓氏结构这种血缘组织结构形式的映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姓与氏的合流。在春秋时期以前,姓是氏族组织的血缘标志符号,其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为了“别婚姻”,维持所谓‘同姓不婚”的制度。同姓不婚制度本是氏族外婚制的一种遗存。凡是同姓,便被认为都属于同一氏族,因而禁止通婚,这种制度在人们刚刚由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同姓者之间事实上的血缘关系还很密切的时候是有意义的,人们也能够自觉地遵守。但是随着世代的推移和人口的繁衍,在若干年代以后,那些不属于后世同一家族的同姓者之间的共同血液成份便会越来越少,最后几乎等于没有,也就是说,姓所代表的血缘关系与人们的实际生理血缘关系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距,这时再以姓来规范人们的通婚范围便不再合时宜,同“姓’不婚已经成为人们婚姻上的障碍,人们必然要冲破它的束缚。
春秋时代同姓之间通婚的事例相当多,仅在一部《左传》中便可以找到诸多证据,例如晋、卫、吴、鲁四国同属姬姓,然而四国间的通婚往来却颇为频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将嫁女于吴”;襄公二十六年,“卫人归卫姬于晋”;哀公十一年,晋悼公孙女跟随其父流亡在卫国,卫大叔懿子“止而饮之酒,遂聘之”;哀公十二年,“(鲁)昭公娶于吴”。此外,晋献公娶狐姬、贾姬、骊姬(见《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以下引自《左传》者均不再注明出处),晋平公娶四位姬姓女子(昭公元年),齐崔杼娶东郭姜(襄公二十七年),齐卢蒲癸娶庆舍女(襄公二十八年),齐公孙明娶国姜(昭公四年),等等,这些都属于同姓间的通婚。这种同姓间的婚姻行为虽然屡屡遭到保守旧礼制者的批评和规谏,但是违反禁忌者依旧有增无已,这说明姓原来所代表的血缘关系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调和,用姓原来所代表的血缘关系来划定人们通婚的界线已经落后于时代,人们迫切希望调整姓所代表的血缘关系,使之与人们的实际生理血缘关系相契合。
与同姓不婚制度遭到破坏的同时,姓的另一项职能,即维护同姓相亲的职能也在丧失。同姓相亲的观念也是氏族时代氏族成员间有相互提供帮助、保护和代偿损害的义务的一种遗存,与同姓不婚制度一样,同姓相亲的观念在人们刚刚脱离氏族社会、同姓的规模还不是很大的时候是有意义的,西周初年的周人上层统治者也曾依靠这条原则维护了自己的统治。但是在进入春秋时期以后,随着同姓间血缘关系的日渐疏远,同姓相亲的观念也日渐废弃,此时,当遥远的血缘联系与现实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人们很少会顾念到同姓之情,比如,晋国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区域,不惜灭掉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等同姓小国(襄公二十九年),而当晋公子重耳落难流亡时,郑、卫、曹等同姓国家对他也同样‘不礼焉’(僖公二十三年),发展到城濮之役的时候,曹、卫两国甚至已经和异姓的楚国站在一起成了晋国的死敌。在春秋时代的史书中,这种虽同姓亦不相亲甚至相害的事例举目皆是,人们对于同姓相亲观念的淡漠和废弃,与同姓不婚制度的破坏出自同样的理由,即姓所规定的人们间的血缘互助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进行互助的血缘关系范围,超出了人们愿意做到和有能力做到的范围。姓原来所标志的遥远的血缘关系己不再为人们所承认,人们正在积极寻求使姓所标志的血缘关系与人们实际生理血缘关系相契合的途径,姓氏合流于是成为必要。
考察典籍中同姓通婚的例子,我们发现,春秋时代的同姓通婚者虽多,但却都是在分属不同家族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也就是说,都是在不同的“氏”之间进行的,绝无同“氏”通婚者;而血缘互助的观念在同家族之内也还严格的保持着,《周礼·地官·调人》云:“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亦云:“父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这都是说明血缘互助的观念在同家族之内还有相当强固的力量,同“氏”相亲的观念还被人们自觉地遵守着。原来的同“姓”不婚现在发展到同“氏”不婚,同“姓”相亲的观念如今也只有在同“氏”的范围之内还能维持。这说明,超出“氏”以外的血缘关系都己不再为人们所承认,在当时人的意愿中,“姓”所代表的血缘关系就应当与“氏”所代表的血缘关系相等同,姓与氏的合流因此而发生。
2.大宗氏与小宗氏的合流。西周春秋时期,由于家族组织结构的多级性,致使某些阶层的姓氏结构也呈现多级的特征,即姓下有氏大宗氏中又包含小宗氏,以鲁国姬姓的孟孙、季孙二氏为例,孟孙氏之下又包含子服氏,季孙氏之下又包含公父氏。对于姓氏结构为姓、大宗氏、小宗氏三级的阶层来说,其姓氏结构的变化还应包括大宗氏与小宗氏的合流。春秋时代后期,当家族组织发生瓦解时,首先是小宗分支家族从大宗本家中瓦解出来。小宗家族的氏号也脱离大宗的氏号而独立,《国语·晋语九》载:智宣子欲以知瑶为后,智果谏之,宣子不听。智果知智氏将亡,为了免受牵累,于是“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及智氏之亡也,唯辅果在”。这条材料说明,小宗分支家族只要另立新氏,就表明与大宗本家脱离了关系,可以不再受其影响了。类似的例子还有吴国的伍员,伍员因数谏吴王夫差不听,感觉到将有危险来临,于是私属其子于齐,改称王孙氏(哀公十一年),及伍员被杀,其子果然幸免于难。在当时,有的人为了表明与所从出的家族恩断义绝,也采用了另立新氏的办法,佐传》定公五年载,吴王阖庐的弟弟夫 自立为吴王,阖庐引兵攻之,夫败亡,于是“奔楚,为棠溪氏”。无论是为了避祸还是为了表示断绝关系,上述诸人都采取了另立新氏的办法,这说明小宗氏一经确立,便不再与大宗氏有任何瓜葛,也不再受其任何影响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宗氏作为小宗氏的上级单位已无存在的必要,大宗氏与小宗氏也发生了合流。
合流以后,原来的两级或者三级的姓氏结构便只剩下一级,随着家族组织一步步解体为个体家庭,这仅存的一级名号便冠于个体家庭之上,成为个体家庭血缘关系的标志。
二、姓氏应用规则的变化
与姓氏结构发生变化同时,姓氏应用规则也发生了变化,原先女子是必须称姓的,但从春秋后期开始,“女子称姓”这条严格的规定已开始松动。《左传》哀公三年:“秋,季孙有疾,命正常曰:‘无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南氏生男,正常载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遗言,……曰南氏生男,则以告于君与大夫而立之。”’案南孺子是季桓子之妻,鲁国有南遗(襄公七年),又有南蒯(昭公十四年),俱是以“南”为氏,则南孺子之“南”也应当是她的氏。按照以往女子必须系姓的原则,这位女子的称谓应当是“南+某姓”,而不是称“南孺子”(所谓“孺子”,只是一种宠号,并不是姓),并且下文再提到此人时,也应当如郑武公夫人武姜称“姜氏”(隐公元年),晋襄公夫人穆赢称“赢氏”(文公七年)一样,称其为“某姓+氏字”,但正常却称其为“南氏”,这显然是已经将“南”这个氏名与其所应当称的姓混同起来了的缘故。
又如《左传》哀公六年载,齐景公夫人中有称“胡姬”者,案胡氏本为归姓,《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胡女敬归、齐归可为证明,这里称其为“胡姬”,“姬”显然是姬妾之意,这也是女子称姓制度遭到破坏的表现。再有鲁昭公夫人吴孟子,吴为姬姓,此女当称“吴孟姬”,而鲁昭公只称其为“吴孟子”,不为其系姓,这也是钻了当时“女子称姓”己被破坏的空子。
以上事例虽然还只是零星的、个别的,但它们已经预示着整个姓氏制度都要发生变化,此后不久,新的姓氏制度就全面登场了。
三、合流以后的姓氏制度
合流以后的姓氏制度与旧的姓氏制度相比较,有如下不同:
1.姓氏合流以后,原有的姓、氏(包括大宗氏和小宗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血缘标志符号。我们将变化后表示个体家庭的血缘关系的标志符号称为“新姓”,以便与变化前的“旧姓”相区别。这时,姓就是氏,氏就是姓.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表示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三者在意义上已不存在区别。《韩非子·孤愤》篇云:“(齐国)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晋国)姬氏不制,六卿专之也。”按照合流以前的姓、氏标准划分,“吕”应当是氏,“姬”应当是姓,韩非在此将二者相提并论,可见姓和氏在当时已经没有分别了。再如司马迁作《史记》一书,其在“记述先秦的人物时,很注意交待这个人物本身及其祖先的姓、氏、名,而记述战国以后的人物,则只记其姓名、籍贯,而不再追溯其祖先姓氏”。②这说明他已经注意到战国以前是姓、氏两级制,战国以后则只有新姓一级,并注意在其作品中以不同记述方式表现这种区别。
2.在姓氏合流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是在姓氏制度发生变化以后情况却起了变化,因为合流之后出现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所以这时虽同姓亦不一定有血缘关系。例如,在春秋时期,周王畿内和秦国都有刘氏,周之刘氏原姓姬,与周天子同族,而秦之刘氏却是晋国士会的遗族,原姓祁,二刘氏在姓氏合流以后均转为刘姓,虽同姓却毫无血缘关系可言。又如春秋时期齐、晋两国都有栾氏,齐之栾氏为齐公子栾之后,原姓姜;晋之栾氏则为晋侯之孙栾宾之后,原姓姬。二栾氏后来均转为栾姓,同样毫无血缘关系。东汉王符《潜夫论·志氏姓》篇云:“周室衰微,吴、楚僭号,下历七国,咸各称王。故王氏、王孙氏、公孙氏及氏谥官,国自有之,千八百国,谥官万数,故元不可同也。及孙氏者,或王孙之班也,或诸孙之班也,故有同祖而异姓,有同姓而异祖。”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3.姓氏合流以后,无论男女,其个人的名称都以“新姓+名”的形式出现,与我们今天的姓名形式基本相同。《孟子·尽心下》云:“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这里就已经将姓和名连在一起谈;《韩非子·内储说下》云:“郑桓公将欲袭郐,先问郐之豪杰良臣辨智果敢之士,尽与姓名。”这里就更直接地谈出了“姓+名”是当时的人名形式。此时的女子一般己不再称用变化前的旧姓(除非该旧姓已转化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从文献中所能见到的几个战国时期的女名看,均无称旧姓者。例如楚怀王幸夫人名“郑袖”(《战国策·楚策二》),若按姓氏制度变化以前的称法,郑女姬姓,此女当称“郑姬”,此称“郑袖”,显然是“新姓+名”的称法。又如中山君之美人名“阴简”(《战国策·中山策》),这也是“新姓+名”的叫法。再如赵王幸妾有称“纪姬”(《战国策·赵策四》)者,按纪为姜姓之国,此女若按以前的称法应当叫“纪姜”,“纪姬”之“姬”当为姬妾之“姬”,而非该女子之旧姓也。
与女子一般不称旧姓相反,从前绝不见于男名的旧姓,此时却在男名中出现了(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谓“汉武帝元鼎四年,封姬嘉为周子南君,此男子冠姓于名之始”。认为旧姓出现在男名中是汉代以后才有的事,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姓氏合流以后,旧有的姓与旧有的氏一道转化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其在男名中出现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例如《战国策·秦策五》和《史记·秦本纪》中均提到秦宣太后的母弟(楚国人)名为“戎”,“案”本为楚国之姓,该男子称“戎”,显然是男子称旧姓之例。又如我们在战国时期的姓名私玺中可以找到“子渴”、“子口”、“子鲜颐”、“姜敬”、“姜口”③等男名,其中的“子”,和“姜”也都是原来的旧姓,现在也都出现在战国时代的男名中。
曾有学者认为,新姓氏制度与旧姓氏制度的不同还表现在新姓氏制度出现以后,姓氏即固定下来,子孙万代永远使用这个共同的姓,除非遇到特殊情况,否则不再轻易改变。④对于这种说法,我们认为它有一定道理,但是应当在时间上限定一下,因为在战国、秦汉之际,姓氏还没有像后世这样固定,人们改易姓氏的情形还很常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案秦国的子孙应当女生“秦”或者姓“赢”,而秦始皇却因生于赵国而姓赵,可见当时的姓氏还不固定。又如《史记·酷吏传》:“周阳由者,其父赵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阳,故因姓周阳氏。”《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褒鲁节侯公子宽,以周公世鲁顷公玄孙之玄孙奉周祀侯,……十一月,侯相如嗣,更姓公孙氏,后更为姬氏。”《风俗通·姓氏》:“中垒氏,刘向为汉中垒校尉,支孙以官为氏。”这也都是人们改易姓氏的例子。一直到三国时代,随着封建礼制和道德观念的日益完备,情况才有所改变,姓氏固定才成为制度。
新的姓氏制度在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天。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具体的姓氏有生有灭、有增有减。但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谓的赵、钱、孙、李诸姓,无论在功能上还是在用法上与战国中期的姓氏仍基本上相同。
注释:
①阎晓君:《论姓氏合一》,《寻根》1998年第3期。 1293号,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俞樟华:《<史记>与古代姓氏》,《人文杂志》1991 ④马雍:《中国姓氏制度的沿革》,《中国文化研究辑年第1期。 刊》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⑧罗福颐:《古玺汇编》第1303、1304、1305、1292、
摘自《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作者:张淑一(系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M005文章来源:印象河南网
相关信息
- ·姓名文化的活化石
- ·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 ·西魏北周时代胡姓再行与胡汉体制
- ·我国历史上的姓氏变化与民族关系
-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汉化
- ·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
- ·汉语姓名中的文化内涵小议
- ·汉语姓名与汉民族文化心理特征
- ·汉语姓名地名系统的文化透视
- ·从文化角度论中西姓名的内涵
- ·中国姓氏的来源
- ·古人的赐姓现象
- ·复姓里的历史知识
- ·复姓的来历
- ·从汉族人的姓名透视中国传统文化
- ·从“百姓”看中国古代的姓氏制度
- ·避忌改姓现象述略
- ·春秋战国时代的姓氏制度
- ·“同姓不婚”的实质
- ·《礼记》之正名与中国姓氏文化之关系
- ·姓氏趣闻:有趣的十七个姓氏组合
- ·三大姓追源:古高丽国君也是姓王
- ·战国时姓氏变革:平民有姓 百姓成民众通称
- ·姓的来历约有二十二种
- ·古代“姓”和“氏”严格区别
- ·姓氏起源于母系氏族
- ·朝鲜、韩国、越南为何有那么多中国姓氏?
- ·最小的姓氏:“山”、“死”、“难”、“贶”
著名人物
没有记录!
精彩展示
没有记录!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