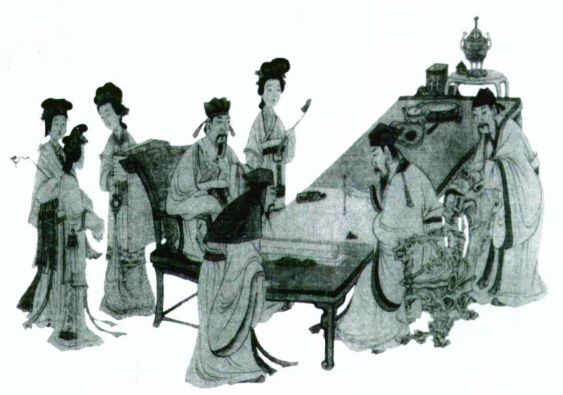精彩推荐
热点关注
专题推荐
-
没有记录!
热点排行
姓氏文化与古代法律
2014/2/11 10:08:46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摘要: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盛行,宗族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姓氏作为宗族血缘的符号和标志,人们赋予其很多的文化意义。这种文化对古代法律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本文就传统姓氏文化与古代的家族制度、与古代的婚姻制度、与立后收养制度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姓氏是家族的名称,个人的血缘符号,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起着一定的作用。在古代,姓氏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封建时代的礼制和法律都对姓氏制度有相应的规范。姓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本文仅就历史上与姓氏有关的法律制度进行初步探讨。
一、姓氏与古代家族制度
马雍先生讲:“姓氏是标志社会结构中一种血缘关系的符号,当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时,这种符号的形式及其应用法则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姓氏制度的沿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性质的转变。”[1]
在封建时代,个人离不开家族,家族的政治、经济实力乃至家族的历史对个人一生的前途命运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个体与家族的这种依存关系集中体现在个人与与生俱来的血缘符号姓氏的关系上。
姓产生于母系氏族时期,代表着一个实在的实行外婚的血缘团体。原始的“姓”是为了“别婚姻”而产生的,这可以从我国的历史传说中得到印证。伏羲、女娲兄妹俩是最早使用姓的人,为“风”姓。王充在《论衡齐世篇》中说,在伏羲之前,人民相当质朴,一般过着“群居野处”的生活,“知其母不知其父”。至伏羲时期,人们走出了蒙昧时代,“知(智)欲诈愚,勇欲恐怯,强欲凌弱,众欲暴寡”,这表明在伏羲之前实行的是族内群婚制。伏羲、女娲之后,开始了族外婚,并禁绝了兄妹通婚。《竹书纪年》记载女娲氏与伏羲同母,女娲“佐伏羲以重万民之别,而民始不渎”,这里所说的“别”即“别婚姻”,“不渎”即指“畏敬渎”,就是说人们开始禁绝兄妹间习以为常的血亲杂乱性行为,认为这是对神灵的亵渎,开始有了乱伦的道德观念。“同姓不婚”成为原始氏族的婚姻习俗。不同的氏族为了与其他氏族相区别,可以有不同的取命方式,有的以图腾取名,有的以地居取名。
氏号大量地产生于西周盛行宗法宗族的时期,它在当时也代表着一个实在的父系的宗法血缘团体。西周是我国典型的奴隶制国家,也是氏号大量产生的时期,我们今天的姓,大多可以追溯到西周。西周奴隶制社会带有浓厚的血缘宗法色彩,周天子按照以“亲亲”定“尊尊”的原则对奴隶主贵族进行一系列程序化的分封,将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分封到全国各地进行统治,每封立一个贵族,既要封土授民,又要赐爵命氏。《白虎通义》:“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闻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为善也。”[2] (P402)氏成为一种社会等级的标志,用以标明人们的身份地位及它所出身氏族的等级。
氏号作为贵族宗族组织的名称,实际上也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这就是人们所谓“氏以明贵贱”。因为这种宗族的身份标志总是按嫡系遗传和继承,但并非所有的直系都能继承和使用这种氏号。比如在各诸侯国,齐僖公之子称齐小白,齐庄公之子称齐仲年,郑厉公之子称郑詹,说明他们在嫡长子继承制下,也有继承君位的潜在可能和潜在权力;相反,当他们一旦另立新氏,说明他们就失去了继承君位的潜在权力和可能性,因为他们不再是公室成员。为了保持公室有一定数量的继承人,公子公孙在世时得氏的情况较少,如果公子在世时得氏,也多以采邑命氏;公孙在世时得氏,也多以父字为氏;而公孙之子在世时得氏最为普遍,氏多以王父字命。无论何种情况得氏,几乎所有的新分立的宗族都是以未继位的公子为始祖的,并在氏号上尽可能地标明其所出身的公子的世系,但不得“上连于公”。王族亦复如是。当然所有的新分立的宗族在等级上都低于其所分出的宗族,他们能够获得多大权力、多少土地以及具备何种身份等级、地位,完全以他们在氏族世系谱上的位置来决定。
西周的贵族一般有姓有氏,但在姓名称谓中,男称氏,女称姓及国。吕思勉先生在《中国制度史宗族》中讲:“人类即知有统系,必有所以表之。时日姓、氏。姓所以表女系,氏所以表男系也。然及后来,男子之权力既增,言统系者专以男为主,姓亦遂改而从男。特始祖之姓,则从其母耳。周制,始祖之姓日正姓,百世不改。正姓而外,别有所以表支派者,时日庶姓,庶姓即氏也。亦日族,随时可改。《大传》日:‘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昏姻可以通乎?系之以姓即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注:‘姓,正姓也。始祖为正姓,高祖为庶姓’。疏日:‘正姓,若周姓姬,齐姓姜,宋姓子。庶姓,若鲁之三桓,郑之七穆。’盖正姓所以表大宗,庶姓所以表小宗也。”[3] (P301)
秦汉以后,贵族的宗法宗族组织纷纷瓦解,出现了历史上崭新的个体小家庭,匹夫匹夫,种田百亩,与这种个体家庭为主导的社会组织结构相适应,出现了姓氏合一。[4]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春秋时犹论宗族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俞樟华也撰文指出:“从《史记》所载战国时人物姓氏看,姓与氏已合而为一,没有区别了,所以司马迁记述先秦人物时,很注意交代这个人物本身及其祖先的姓、氏、名,而记述战国以后的人物,则只记其姓名、籍贯,而不再追溯其祖先姓氏。”[5]至于姓氏合一的原因,并不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司马迁《史记》姓与氏混而为一,自是之后,姓氏不分。”[6](P2048)姓氏非司马迁所能合一,《史记》中的对历史人物记述已姓氏不分,只能是社会上已经流行以氏为姓,姓氏合一的真正反映。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对姓氏的起源、发展以及历代命名的沿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释。他认为“今世姓氏同物,古则不然”。梁启超以社会学观点考察发现:“姓为母系时代产物,氏为父系成立以后产物,姓久已亡,今所谓姓,皆以氏而冒称耳。”
姓氏合一以后,姓氏的变化也显得错综复杂。在历史上有不少因某种原因被皇帝“赐姓”、或因某种原因自行“改姓”的例子,也不断有少数民族融合到汉民族中,采用汉人的姓氏。这样一来,同姓未必同祖同种。相反,异姓也有可能同祖同源。在当今社会,随着男女平等的家庭观念日益深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也不断地出现一些新的姓氏,例如,有一些人在取名过程中往往联合赘以父姓和母姓,改变了以往姓氏按父系继承和遗传的做法。这样以来,同姓除非有明确的世系可以考察,否则很难视为同祖近亲。
二、姓氏与古代婚姻制度
“同姓不婚”是中国古代一项非常严格的婚姻制度。它由原始社会的外婚习俗发展成为西周的一种礼制,再上升为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同姓不婚”除了法律强制实施以外,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婚姻禁忌。
姓在西周时期已不代表任何氏族实体,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别婚姻”,原始社会“同姓不婚”的禁忌已演化为西周的一种礼制。《礼记大传》:“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为了贯彻“同姓不婚”的原则,周代男女在通婚之前,有一个“辨姓”的过程,所谓“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也就是说对通婚的男女双方其祖先所出自的氏族按一定的世系进行一次追查,辨别他们的祖先是否来自同一氏族即是否同姓,其目的是为了确定能否缔结建立婚姻关系,正如郑樵所讲:“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7]也是为了“辨姓”的方便,人们通常将姓加在妇女的称谓中,即“妇人称国及姓”。李学勤先生在《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8]一文中讲:“氏加姓,是女名最常见的形式。”
到了春秋时期,同姓通婚的例子多了起来。《左传》中有很多记载,如庄公二十八年,晋献公有狐姬、骊姬;襄公二十三年,晋平公嫁女于吴,二十五年,崔武子娶东郭偃之姊,二十八年,卢蒲癸娶庆舍之女;昭公元年,晋平公有四姬;昭公二十八年,晋叔向之父羊舌职与羊舌姬通婚;哀公十一年,卫大叔懿子娶晋悼公之孙女;等等。金文中有吴王与蔡大孟姬、吴王光与叔姬通婚的例子。其中崔武子娶东郭偃的例子尤为典型,齐棠公的妻子是东郭偃的姐姐。齐棠公死后,东郭偃驾车载着崔武子去吊唁。崔武子看见齐棠公的妻子,为她的美貌所征服,就让东郭偃从中牵线,欲娶东郭偃的姐姐、齐棠公的妻子。东郭偃说:“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崔武子问卜掐筮的结果都得吉兆。他将吉兆告诉陈文子。但陈文子却说:“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日:‘困于石,据于蒺藜,人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人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陈文子讲的大意是说,齐棠公的妻子命中克夫,劝他不要娶,但崔武子回答:“嫠(寡妇)也,何妨?先夫当之矣。”[9]于是就毫无忌惮地娶了同姓的东郭氏为妻。相比,卢蒲癸娶同姓庆舍之女时则更振振有词,庆舍之士对卢蒲癸说:“男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卢蒲癸的回答耐人寻味,他说:“宗不余避,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1O]这说明在春秋时期,“姓以别婚姻”的社会作用已逐渐消失。清人赵翼说:“同姓为婚,莫如春秋最多。”由于姓所反映的血缘关系有的已很遥远,而且姓的数量有限,长期不变,这势必影响了人们的通婚要求,因此“同姓不婚”的禁忌迟早被打破是势之必然。
姓氏合一以后,婚姻关系的建立也遵循“同姓不婚”的原则,但与先秦的“同姓不婚”有本质的区别,先秦“姓同氏不同”,不得通婚;“氏同姓不同”则可通婚。而这时所谓的“同姓不婚”实际上是春秋时期的“同姓共宗不婚”,也就是同宗同氏不能结婚。正如郑樵《通志·氏族略》:“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明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以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7]
《北史·魏文帝纪》诏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政因事改者也。是殷之五世为限,其法亦承于夏,殆上古之禁令皆然。至周法始定为百世不通,视古为密,然亦指受姓之同出于一祖而言。其非同出一祖者,自不在范围之内。”[11]
《周书·武帝纪》:三年二月丁卯,诏曰:“同姓百世,婚姻不通,盖惟重别,周道然也。而娶妻买妾,有纳母氏之族,虽日异宗,犹为混杂。自今以后,悉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妻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12]
《唐律》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疏议》日:“同宗共姓,皆不得为婚,违者,各徒二年。然古者受姓命氏,因彰德功,邑居官爵,事非一绪。其有祖宗迁易,年代寝远,流源析本,罕能推详。至如鲁、卫,文王之昭,凡、蒋,周公之胤。初虽同族,后各分封,并传国姓,以为宗本,若与姬姓为婚者,不在禁例。其有声同字别,言响不殊,男女辨姓,岂宜仇匹,若阳与杨之类。又如近代以来,或蒙赐姓,谱牒仍在,昭穆可知,今姓之与本枝,并不合共为婚媾。其有复姓之类,一字或同,受氏既殊,元非禁例。”[13](P262)
事实上,“同姓不婚”已成为一种文化禁忌。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同姓即同祖,“五百年前是一家”,有血缘关系的人通婚是男女无别、与禽兽无异的行为,因此被视为婚姻之大忌。《礼记·曲礼》日:“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郑注:“为其近禽兽也。”《左传》:“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杜注:“蕃,息也。”孔疏:“违礼而取,故其生子不能蕃息昌盛也。又昭元年: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杜注:“殖,长也。同姓之相与先美矣,美极则尽,尽则生疾。”孔疏:“同姓相与先美,今既为夫妻,又相宠爱美之至极,仕先尽矣,乃相厌患而生疾病。非直美极恶生疾病而已。又美极骄宠,更生妒害也。”刘炫日:“违礼而娶,则神人不佑,故所生不长也。晋文姬出而霸诸侯,同姓未必皆不殖。此以礼法为言,劝助人耳。”又云:“人之本心,自然有爱,爱之所及,先及近亲。同姓是亲之近者,其爱之美必深,是同姓之先与自美矣。若使又为夫妻,则相爱之美尤极,极则美先尽矣。美尽必有恶生,故美尽则生疾。此以为防,推致此意耳。”《三国志·魏书·陈矫传》:”陈矫字季弼,广陵东阳人也。”注引《魏氏春秋》日:“矫本刘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庭议其阙。太祖惜矫才量,欲拥全之,乃下令曰:‘丧乱已来:风教凋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谤者,以其罪罪之。’”[14]
同姓者未必同源同祖,即使如此,同姓不同宗者因年代久远,血缘关系早已淡化。有些出于现实婚姻的需要出发,往往打破“同姓不婚”的禁忌。如清代史学家赵翼在《詹曝杂记》中的“甘省陋俗”条记载:“甘省多男少女,故男女之事颇阔略。兄死妻嫂,弟死妻其妇,比比皆是。同姓惟同祖以下不婚,过此则不论也。”[15](P76)民国时期,“直隶各县,向有同姓结婚之事,案牍中如李李氏、刘刘氏等,数见不鲜。查同姓为婚,律所不许,但此种习惯行之既久,已为社会上普通之惯例,然皆以不同宗为制限条件。大概此种习惯,不仅直隶一省为然,即长江以北省份,亦多如是也。”[16](P759)“同姓为婚,律所不许。惟甘肃人民婚姻多不避同姓,势难依律禁止。按:前项习惯系甘肃第一高等审判分厅刘会员所报告。据称,审判案中,如王王氏、李李氏、张张氏等,屡见不一。且甘省回民最多,而回民中姓马者,又居十之八九,回汉之间,以汉女嫁回男者,偶或有之,若回氏,则绝对不嫁汉男,回民如避同姓为婚,势必至女无从嫁,男无从娶,故所谓马马氏,几至屈指难数。积习相沿,牢不可破。”[17](P1035 - 1036)
事实上,由于姓氏在遗传继承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变异,正如上文所论及的,同姓未必同族,因此所谓的“同姓不婚”就渐失本意。吕思勉说:“古者近亲,必为同族。……同姓不婚,源于同族不婚,则诚得近亲不婚之意。后世则但求不同父系,姑之子,从母之子.无不可婚者。……而后世之所谓同姓不婚者,亦全失近亲不昏之意矣。”[3](P285)有鉴于此,清末沈家本曾上(删除同姓为婚律议),他说:“以古义而论,当以同宗为断,而以《唐律》为范围。凡受氏殊者,并不在禁限。娶亲属妻妾律内既已同宗无服之文,则同姓为婚一条,即在应删之列,正不必拘文牵义,游移两可也。”[18](P2051)
责任编辑:M005文章来源:印象河南网
下一条:姓氏中的文化现象解读上一条:姓氏合流论略
相关信息
- ·姓氏合流论略
- ·姓名文化的活化石
- ·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 ·西魏北周时代胡姓再行与胡汉体制
- ·我国历史上的姓氏变化与民族关系
-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汉化
- ·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
- ·汉语姓名中的文化内涵小议
- ·汉语姓名与汉民族文化心理特征
- ·汉语姓名地名系统的文化透视
- ·从文化角度论中西姓名的内涵
- ·中国姓氏的来源
- ·古人的赐姓现象
- ·复姓里的历史知识
- ·复姓的来历
- ·从汉族人的姓名透视中国传统文化
- ·从“百姓”看中国古代的姓氏制度
- ·避忌改姓现象述略
- ·春秋战国时代的姓氏制度
- ·“同姓不婚”的实质
- ·《礼记》之正名与中国姓氏文化之关系
- ·姓氏趣闻:有趣的十七个姓氏组合
- ·三大姓追源:古高丽国君也是姓王
著名人物
没有记录!
精彩展示
没有记录!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