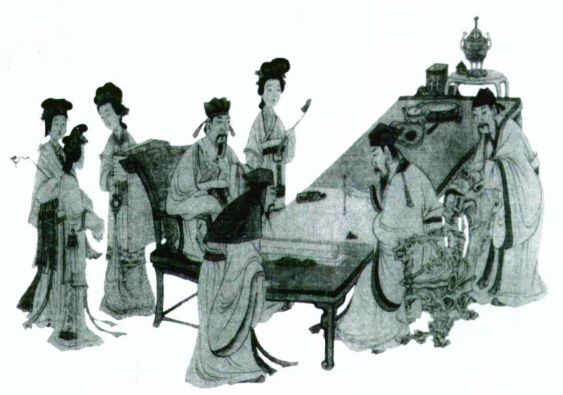精彩推荐
热点关注
专题推荐
-
没有记录!
热点排行
中国古代婚姻演变与姓氏源流问题(上)
2014/2/13 14:27:04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一、问题与方法
我国古代的姓氏源流问题,是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学科都涉及的重要内容。对此,学术界历来大都赞成“先秦时期‘男子称氏、妇人称姓’,秦代之后才有‘姓氏合一”’之说。就此观点诸如:
1.(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曾概说:“三代之前,姓氏一分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蛮此道犹存。古之诸侯诅辞多曰、坠命亡氏,踣其国家’,以明亡氏则与夺爵失国同,可知其为贱也;……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其《氏族略序》又针对《史记》以“姬昌”称周文王,以“姬旦”称周公持异议,他认为“三代之时无此语也”,“姬”为周文王和周之姓是不对的,三代之时男子有氏而无姓。据此,郑樵上述所言的“三代之前”是指秦之前的夏、商、周三代,而“三代之后”即指秦代以后。这样可知,郑樵是持先秦时期“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先秦之后才有“姓氏合一”之说的。
2.(明)顾炎武在<原姓》中说:“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一再传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姓者乎?而称姓者乎?无有也”。
3.(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姓氏》中也明言:“三代以上,男子未有系姓于名者,汉武帝元鼎四年。封姬嘉为周子南君。此为男子冠姓于名之始”。
4.现在我国许多人都认同上述观点,如最近楚战国、楚天骄撰写的《华人姓氏与地名之关系研究》一文中,在引用郑樵关于姓氏的上述一文后指出:“秦汉以后,姓氏不别。而正是把‘姓’与‘氏’混为一谈,是从汉代司马迁开始的”①。
上述是持先秦“男子称氏,妇人称姓”,秦代之后才有“姓氏合一”之说的几个典型论点。历来我国学术界关于姓氏源流的研究基本上是承诺了上述说法而进行的,并把论题转向其状况和原因的探讨上。而对其原因的研究,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春秋时贵族男子之所以不称姓,是因为姓与生俱来,言氏则可知姓。也因为始祖之姓已很久远,单表始祖之姓已不能表示现有身份,因此就必须让人知道其姐父为何人,这是称氏的关键所在”②。而就这一观点也有人质疑,如夏无培先生提出:“其一,上古命氏方式多样,除了祖先的字或溢命氏外,还有以官为氏,以封邑为氏等方式,而以后两种情况显然不一定知道‘祖父为何人’;“其二,史实表明,不同姓的家族可能会有相同的氏名。例如,春秋时期的孔氏至少有三个:一在卫,姞姓;一在厥,姬姓;一在鲁,子姓。在这种情况下,怎可‘言氏知姓’呢?”并认为:“既然姓的作用是‘别婚姻’,那么贵族男子可以只称氏不称姓的缘由也应从婚姻方面去找。自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血缘世系均按男子计算,宗法制社会以男子为中心更不待言。在宗法社会中,婚姻的终极目的和最高准则是‘上事宗庙,下继后世’,基于此,对同姓结婚所造成的‘不蕃’、‘不殖’的后果最关心的也是男子。事实上,即使在春秋时期,只要男方不计较,他完全可以娶同姓女子为妻。晋文公母大戎狐姬为姬姓之女,与文公之同姓,姬姓的鲁昭娶同为姬姓的吴女为妻,都是这样的例子。正因为婚姻的根本目的与男子家族密切相关,故缔结婚姻时,男方总是主动的一方,这从周代婚姻的‘六礼’中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可以说,在当时,只存在男方是否‘娶同姓’的问题,不存在女方是否‘嫁同姓’的问题。既如此,男子当然称氏即可,不必称姓了③。
这里,夏先生主张从“婚姻方面”来解释上述问题,这一思想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仅局限于周代的“宗法制度”考察,并认为仅存在男子是否“娶同姓”问题,不存在女子是否“嫁同姓”问题,而由此判定之所以男子称氏而不称姓。我们以为此解仍是不足为信的,质疑有二:
(l)三代之时,我国社会早已处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这对血缘关系已完全由男子来计算,而计算血缘关系的单位(标记)自然就是有标征血缘关系的“姓”。如果说,三代时期男子称氏而不称姓,而其中“氏”只有“明贵溅”之作用而无“别婚姻”之功能,这时处于个体婚的男子没有“姓”的相对所属或命名,那么又如何“别婚姻”呢?从历史逻辑上讲,应该说三代时男子也应有“姓”的。这一点,我们从史料上看,《左传·僖二十三年》载:“男血同姓,其生不蕃”。《国语·晋语四》中也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这里《左传》明确提到“男女同姓”,又何硬称当时“男子无姓”呢?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婚姻基本上已处于个体婚为主的状态,婚姻具体上是个体男女之间的事,男子若无“姓属”怎能“别婚姻”呢?这就不能忽视三代的男于有姓的实际。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清楚地记载:“禹为姒姓”。这里所言的“禹”是男子而非女子。大禹治水的传说中也描述“禹”为男子。而《山海经·海内经》中所传,禹奉命治水经涂山时与涂山氏女子结了婚,后生有儿子启。禹作为夏代第一代王启之父,是男非女。据此,夏代男子有姓,属实。而朱绍侯先生在针对夏之前的炎、黄两帝考证指出;他们同出少典氏的两个部落,分别为姬姓和姜姓,并相互通婚④。这里,炎帝和黄帝均被认为有姓,都是部落男姓首领。是故,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史实上讲,在三代时或更早些时候男子都应有姓的。那么,我们这里要考虑的不仅是先秦三代男子为何称氏不称姓,而女子称姓不称氏的问题了,而还应该考虑郑樵在《通氏·氏族略序》中所提的“三代之前,姓氏一分为二”中的三代之前是否是指先秦之前?根据上述推理及例证,我们以为此句中的“三代之前”应指夏、商、周之前,而非秦代之前。只有在夏、商、周三代之前,“男子称氏,妇人称姓”之说才可符合逻辑的解释。这样,我们考察“男子称氏,妇人称姓”不应把视界仅放在三代之时,而应往前推。只是关于“姓氏合一”问题不能忽略三代之时罢了。另外,“姓”到了父系社会时期,尤其三代时期,它不再是母系血缘共同体的标记,而是父系血缘共同体的标记,并且“姓”已演化为个人命名的主要依据和形式。这样,实际上母系时期和父系时期的“姓”,是有内涵区别的。以往人们研究“姓氏”时不太注意到这点,这是导致“姓”源流认识不清的原因之一。
(2)关于“氏”的问题。首先必须区别、弄清作为族群共同标记的“氏”和作为个人命名的“氏”及其联系。朱绍候先生在《中国古代史》(上册)中指出:“我国古代有严格的姓、氏区别。……姓是标志出生的血缘关系,最初是从女性来确定。在‘同姓不婚,的限制下,一个姓即是一个通婚单位。由于人口增殖,于是原来作为氏族标志的姓,就扩大成为这些近亲民族共问标志,而在同一部落内的各个氏族,又必须各有新的标志,这就是“氏。”⑤而《左传•隐公八年》中则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疾。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无疑,这里所举的两种“氏”,是两种不同情况的“氏”。前者是作为大部落内小分支的共同标记,是母系氏族时期的产物;后者则是个人命名中的“氏”,是父系氏族时期的产物。过去我们论说“氏”时没有区别二者,导致一些问题模糊不清。另外,作为共同标记的“氏”和作为个人命名的“氏”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我们认为,后者系前者演化而来。这一点也和“姓”一样,最初是集团的共同标记形式,后来则慢慢演化为个人命名(标记)的形式。那么,关于“氏”的源流则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三代之时”的视城内,并把它只当作个人命名的形式来进行考察,而要看其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的整个演变概况。
鉴于上述两点分析,我们以为,关于姓氏源流问题的研究,涉及到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变化的整个过程,并且与“婚姻体制”的演变密切相关。因此,就这一问题的探讨,必须基于古代的社会环境,以考察其婚姻关系的变化为钥匙,并借助于民族学的知识,才能真正地弄清古代传承下来的“男子称氏,妇人称姓”之说以及有关姓氏源流问题。
二“族外群婚”和“姓”、“氏”的起源
人类最初的性关系是没有婚姻体制的,属于一种杂交状态,但是由于“生物自然选择法则”的作用,人类的性关系在历史发展中必然由杂交向同辈婚过渡,再由同辈婚向族外群婚过渡,以及经过对偶婚后才使个体婚最终确立。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人类社会发展的层次——体现在婚姻关系上进入了族外群婚阶段。这是许多中外史家在考证母系氏族社会状况所共识的。那么,婚姻形态的不断衍进,其动因是“生物自然选择法则”。关于“生物自然选择法则”的遵守,它明显地发展和进入成为人类自觉操作行为阶段,其标志是在婚姻生活中走入了自觉辨别血缘亲疏和以此作为依据建立人类婚姻关系的时期。“生物自然选择法则”的过程中,使先民在婚姻生活中逐渐认识到非近亲婚配比近亲婚配更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繁衍)。这样,人们基于“优胜劣汰”的选择原则,逐渐形成了以区别“血缘亲疏”而进行婚配的观念和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同的氏族间进行区别血缘关系、明确自身的命名就发生了了最初人们在追溯自己氏族的血缘起源对,是走向利用某一动物等之类的外在物种怍为氏族血缘关系及其集团进行确认、鉴别和标证的。这种对自身氏族认知的原始思维的结果,即是图腾的产生。关于这一点,刘文英作过深入的研究并提出:原始图腾崇拜的实质是先民用以标征与确认人类血缘氏族团体自身的象征符号@。我认为这一说法是正确的。而图腾作为氏族血缘确认的一种符号,它就是“姓”的前身。图腾作为一种血缘确认符号,它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演化作为氏族自身进行“命名”的符号时,即“姓”就产生了。人类学的许多调查资料已证明有由“图腾”过渡到“姓氏”的事例。如台湾白马人最早的一批姓氏,无不取之自图腾。当中如杨(羊)姓是白马人最大的宗支,杨姓源于的羊曾是白马人的祖先的总图腾⑦。而高山族的“姓氏制颇奇。太么族及阿眉族无姓,他族有姓;其姓大部为‘太阳’(Taihira)、‘蝉’(Camraral)、‘狸’(Paptal)等⑧。林惠祥先进研究认为其姓有图腾遗意。可以肯定,“姓”最初是由“图腾”演化而来的,并二者均反映了以“别血缘”为宗旨并由此来对自身确认和命名的性质。“姓”发生和成为氏族集团的共同标记,它和前期的“图腾”演化而来的,并二者均反映了以“别血缘”为宗旨并由此来对自身确认和命名的性质。“姓”发生和成为氏族集团的共同标记,它和前期的“图腾”一样,都是人类初期在婚姻生活中遵循“生物自然选择法则”所进行自身血缘确认、区别的行为结果。一般个体人都根据其出生而被纳入特定的“姓”的规范中,从而获得血缘确认的社会标征。而在具体的历史时限上,“图腾”衍化过来并成为氏族的命名符号,是在母系氏族时期。《商君书·开塞》中记载:“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这描述了母系社会时的婚姻及人们的血缘归属状况。而关于“姓”,甲骨文从女从生会意,表示“女所生”,即指母系氏族社会中同一个老祖母而生的后代为同姓。汉代《白虎通义·姓名》中说:“姓者,生也”。“姓”的本义就是源于同一女性始祖的族属共同所有的符号标记,是人的血缘系属标志。因此,“姓”开始出现时,姓的内涵首先是作为不同氏族血缘集团的标征符号,并主要作为“别婚姻”之用的依据。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说:“姓之所以别婚姻”,明确“姓”为“别婚姻”之用,这是无疑的。事实上,历来“姓”一直是人们“明血缘”、“别婚姻”的主要依据,传承至今不变。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母系氏族时期,“姓”是属于母系氏族集团的族群标记,“姓”是否仅属于女子或男子也享有吗?从传统所说“三代之前……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来看,“姓”作为共同标记只是针对氏族中女子而言。我国上古八大姓,即姬、姜、姚、姒、姞、赢、妫、坛,均是从“女”字的,可见母系氏族社会时,“姓”专属于女子而非男子。那么,为什么那时只有女子享有“姓”的标记的权利,而男子没有呢?而实际的婚姻生活又必然是由一方氏族的男子与另一方氏族的女子结合才成立。因此,男子实际上参与婚姻丽又不具对作为“别婚姻”的“姓”权利的享有,这就出现了“怪事”了。为此,破译这一“迷码”是解开为什么出现“男子称氏、妇人称姓”以及姓氏源流问题的一个关键步骤。
其实,当时的婚姻在“明血缘”上只是女子集团之间进行“区别”的事,而非女子与男子之间的事。“姓”作为“明血缘”、“别婚姻”的依据,它本身在母系社会中指谓女子氏族集团的,而非个体女子。那时婚姻作为群婚并不需要区别个体而只是区别群体。故它是某一女子集团与另一女子集团间进行“区别”之需要而存在的。那么,男子为什么不能作为“明血缘”、“别婚姻”的要素呢?这显然与当时社会的生产、生活及男女构成的社会地位、关系有关。
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人类的生活主要靠采集、种植和狩猎为主,而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出现了男女分工,一般女子专司采集、种植和哺育子女;男子专司狩猎等。相较而言,女子的工种对于氏族生活相对有保障,而且哺育子女显示出延续氏族的重大意义;而男子工种则无保障,而在人类延续上的作用又没有得到确认。由此就造成了女子优势,男子弱势的社会关系及地位。当婚姻体制进入“族外群婚”时,为适应这一婚姻需要,就促成了男子在成年后处于“族外居”的情况,即男子成人后就必须被派送到有婚姻关系的氏族集团中去居住(生活)和参与生产活动。事实上,在母系氏族时期,一个氏族繁衍下来的男女,在生产、生活上形成了女子“从内居”、男子“从外居”的结构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及地位。关于这一点,郭沫若先生曾作过论述。他指出:“按照母系氏外婚制,本氏族的兄弟姊妹不能通婚。兄弟必须出嫁,在相互的对方氏族的女子中寻找配偶,同样,对方氏族中的成年男子则嫁到本氏族来,在本氏族的女子中寻找配偶。出嫁的男子死后,都分别归葬于各自的出生氏族,而按照氏族内不许通婚的制度,他们也不能跟本氏族的姊妹同墓合葬。反之,姊妹只能从外氏族娶夫进来,她们死后同样不能跟本氏族的兄弟合葬。但同性合葬或男女分区埋葬则是许可的⑨,从“葬俗”的情况看,我国处母系氏族时期的临潼姜寨村落遗址考古所发现的“二次迂葬”也可证明上述这一点。遗址考古发现,村落的“所有氏族成员,死后都埋葬在公墓地里。当时盛行单一葬和合葬。合葬是男女分区埋葬,男子大都是二次迁移集体葬。有母子合葬,而没有一对成年男女合葬和父子合葬”⑩。朱绍侯先生对此明确指出,这是因为母系氏族集团中“她们的对偶,则是其他部落的男子,死后大都要分别归葬到原来所属的氏族墓地葬,所以多为二次迁葬⑾。”我国古代文献《尔雅·释亲》关于亲属称谓制度的记载也反映了母系氏族婚姻关系的遗迹。古时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女子谓舅弟之子为‘姬’,谓出之子为‘离’,谓姪之子为‘归孙’。而之所以这样称谓是因为,姊妹之子必须从本氏族出嫁到对方氏族中去,故称之为“出”,而“出”之子不出于本氏族,但以辈份而论为孙,所以叫“离孙”;另又因兄弟出嫁到对方氏族,与对方氏族女子所生之子,由于结婚组合的规定,一定要嫁回本氏族中来。所以称为“姪”,“姪”即“至”之意。姬之子又生于本氏族,所以就叫做“归孙”⑿。总之,从上述材料可证明,母系氏族时期一个氏族繁衍下来的男女人们,是女子“从内居”而男子“从外居”的。
正是由于女子“人内居”和男子“从外居”的生活方式构成了母系氏族时期男女间地位的差别性,其主要表现在:(1)氏族组织权力属于女子,而不属男子。因为男子处于“从外居”的境况,氏族内未成年的男子属于将被派出去的成员,而成年的男子都是外部嫁进来的。成年男子是外来的,故在氏族内部生活中是从属的,他们与氏族不是一开始就有经济联系,以至实际上作为后来者(附属单位)而没有发言权、主宰权,而只能从属于所迁入后的氏族中的这一群女子生活。(2)男子弱势地位的社会结构同样映衬在婚姻关系上,尽管男子是婚姻中的重要单位,但是男子仅作为一种“性”的角色存在,即只是生物性质的本能作用的承诺,而未取得社会性质的承诺。实际的婚姻操作中,只是一群女子与另外一群女子如何选择和派送男子的问题,而不是男子与女子间的选择和结合问题。因此,在母系氏族社会中,进行“血缘亲疏”的辨别,只是在女子氏族集团间交换男子时才需要的。这样,“姓”作为“明血缘”、“别婚姻”,实际上是女子氏族集团为区别于其他氏族而对自己氏族全体成员进行血缘规范、标记的符号。不同的女子氏族集团有着不同的“姓”。在婚姻操作中,对“近亲血缘婚配禁忌”的遵守,就表现为“同姓”的女子氏族集团间不交换或派送男子,而在“异姓”的女子集团间则交换派送男子。可以肯定,“姓”最初是专属于女子氏族集团的,而非个人的,更不属于男子和男子个体。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国古代曾有女子称姓而男子不称的缘故了。
其次,关于“氏”的起源问题。我们上文已指出我国古代实际有着两种“氏”的存在,即最初作为氏族集团的“氏”和后来作为为个体命名的“氏”。“氏”的起源,当然是以最初形态为形式而发生与存在的。在具体上,关于“氏”的产生,大多数认为它是“姓”的分支。我认为这是无疑的。古文中“氏”与“支”同音,借“氏”为“支”,“氏”具“支”的含义,在内涵上往往表示某一氏族的图腾、部落符号等⒀。《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禹以姒姓”,同一姒姓之下又分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率氏、冥氏、斟戈氏”。可见,一个大姓氏族分为若干个分支散居各地,各个分支又有自己的特殊的称号作为标志,这就是“氏”。“氏”作为“姓”的分支已无疑。那么“氏”的社会意义及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此,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说:“三代之前,……氏以别贵贱”。而“姓所以别婚姻”,“三代之后,
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这已明确指出了“氏”最初的本质和用途,即“别贵贱”之用。那么“氏”何以产生并成为“别贵贱”之依据呢?众所周知,最初的“氏”的作为一个大“姓”下分化下来的分支集团,可以理解它是“姓”内部各女儿集团之间进行相互区别的符号。而同一“姓”分化下来的各“氏”之间,当然没有必要进行血缘区别,那么“氏”是区别什么呢?无疑就是区别各女儿集团——即各氏之间的地位问题。当然,“氏”作为“别贵贱”,其功能最初只是针对同姓内部而没有超出同姓之外,即是“姓”的内部产物和作用于“姓”之内部。《左传·隐公八年》中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这里讲的“氏”春秋战国时期的事,但可从中看到“氏”在氏族生活中,它的初始作用是作为“胙之土”而存在。“胙”在句子中的含义,《辞海》中·释为“赐”⒁。那么,“胙之土”即为“赐给的土地”。由此可见,古代“命氏”与赐封土地密切相关。可以理解,母系氏族时期,一个大“姓”的部落集团中,分化出各个等次的女儿集团出来,当他们散居各地时,他们所获许居住、生活的地方是由大姓部落的分赐而认定的,并且根据所赐的土地而立徽号——氏,用以标征这一个女儿集团的地域位置和享有权利。而土地本身因自然环境的状况和人工开发的程度而呈现好坏之分。因此,部落联盟中给女儿集团氏族分赐土地时,就存在优劣的等级差别问题。那么,大姓下的各女儿集团依据其在“大姓”中的社会地位而获得不同的土地占有,以至赐封土地的本身就包含着等级之分了。这样,因“胙之土而命之氏”的“氏”,当然就同时标征着它自身在享有土地中所蕴含的等级权力状况。历来我国常用“地位”一词来表征一定的人或集团在社会关系中的贵贱、权力大小等等状况,其实这一词的内涵来于上述的历史的约定俗成,即是古代“氏”各族(女儿集团)在大姓部落中受赐中居住的土地所包含的等级引申而来的,借用“土地位置”的指谓来指示“社会关系”的含义,即“地位”由地理性概念转化为社会性概念。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氏”最初是作为“别贵贱”,而不是作为“明血缘”出现的了。当然,“氏”后来逐步演化并与“姓”合而为一,又形成了“皆以别婚姻”,这是后话。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姓”最初属于女子氏族集团的共同标记,“氏”为“姓”的分化,是大姓下女儿氏族集团的标记。那为什么“氏”最初属于女子集团标记,而后来则变为男子的标记了呢?即后来呈现出“男子称氏”的局面呢?我们以为这涉及到“氏”的流变问题,事实上“氏”经历着先作为女子氏族分支集团的标记转化为氏族中男子进行标记的过程。以前关于“氏”的研究,人们未注意到“氏”的这一变化,只是一开始就把“氏”当作男子的标记而待,因此就出现了难解之迷,甚至误解,而“氏”由女子的标记变作男子的标记,这一演变与社会发展尤其婚姻关系的进化直接有关。我们务必就此深入研究,才能更好地弄清姓氏的源流问题。(未完待续)
注释:
①⒀楚战国、楚天骄:《华人姓氏与地名之关系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②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中国文化史三百题》,第33页。
③见《长沙电力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的1期,第122页。
④⑤⑩⑾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5页,第14页,第26页,第27页.
⑧刘文英;《从原始思维看图腾之迷》,《哲学研究》,1995年第11期。
⑦邓廷良:《白马人的姓氏》,见《民族文化》1984年第6期。
⑧《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63页;见高民强《神密的图腾》,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⑨⑿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4页,第46页。
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3页。
摘自《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9年4月 第17卷第2期 作者:刘宗碧(系黔东南民族师专民研所助研员)
责任编辑:M005文章来源:印象河南网
下一条:中国古代姓氏文化变革中的社会政治因素上一条:中国古代赐姓赐名制度考论
相关信息
- ·中国古代赐姓赐名制度考论
- ·战国私玺中所见古代复姓及源流考
- ·元明蒙汉间赐名赐姓初探
- ·元朝汉族及内迁各民族的姓氏来源与变化
- ·由姓氏制度的发展看两周宗法制的兴衰
- ·演变中的中国姓氏
- ·姓氏中的文化现象解读
- ·姓氏文化与古代法律
- ·姓氏合流论略
- ·姓名文化的活化石
- ·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 ·西魏北周时代胡姓再行与胡汉体制
- ·我国历史上的姓氏变化与民族关系
-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汉化
- ·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
- ·汉语姓名中的文化内涵小议
- ·汉语姓名与汉民族文化心理特征
- ·汉语姓名地名系统的文化透视
- ·从文化角度论中西姓名的内涵
- ·中国姓氏的来源
- ·古人的赐姓现象
- ·复姓里的历史知识
- ·复姓的来历
- ·从汉族人的姓名透视中国传统文化
- ·从“百姓”看中国古代的姓氏制度
- ·避忌改姓现象述略
- ·春秋战国时代的姓氏制度
- ·“同姓不婚”的实质
- ·《礼记》之正名与中国姓氏文化之关系
- ·姓氏趣闻:有趣的十七个姓氏组合
著名人物
没有记录!
精彩展示
没有记录!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