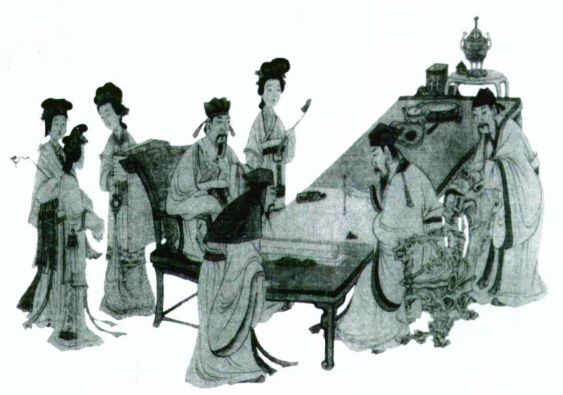精彩推荐
热点关注
专题推荐
-
没有记录!
热点排行
春秋战国时代的姓氏制度(2)
2014/1/7 14:07:38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以上所引述的史例,说明了姓氏制度发生变化的历史前提。表面上看来,同姓通婚无足轻重,但它却足以引起下列连锁性变化。它不但使所以别婚姻的姓失去作用,亦使同姓和异姓的族界发生混乱;它不但使姓所具有的明其祖之所出的作用丧失,更重要的是它使以距离始祖远近的关系来划分等级的宗法制度陷入绝境,亦使宗主的地位动摇下降,上述的“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恶识宗”的记载,就是这种现象的说明。这样,作为“千万年不可变”的姓,由于同姓的通婚,就丧失了往日严格宗法制度、使异姓附于同姓、小宗尊从大宗的社会作用。同时,春秋末年的世官世族和世卿世禄制度,亦被只享有实物俸禄的士夫式新生官僚制度所取代,百官就是“百姓”的旧制巳弃而不用。另一方面,也因在社会动乱中,“众庶之家或避国讳、遁仇逃罪,变音易姓者,便可皆言始祖正姓”[34]。因此,姓在春秋晚期巳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和意义,变为无足轻重的、单纯的、家庭或个人的代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百姓”一词,已包括了丰富的社会变化的内容。史书记载:
“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35]。
“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此厉民之道也”[36]。
“民”字与“百姓”一词已意义相同而通用,说明庶民在当时有相当部分已有了姓。《墨子》一书对此也多有记载。
“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37]。
“观其国家、百姓、人民之利[38]”。
此处的“百姓”一词,已是受掠夺、被征敛的对象,绝非往日身为贵族的“百姓”。按“刑不上大夫”[39]的古制,“百姓”在春秋时代是不受法律支配的特权阶层,但战国时代的“百姓”则受制于法律了。“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40]。“有司”即是官职之称,“百姓”已非官职之代称,其身份已是受法律统治的庶人。又:“治安百姓,主之则也;教护家事,父母之则也”[41]。“百姓”又成为治安的对象,与“家事”对言,当已变为一般家庭中的成员了,改变了它在西周春秋时代所长期具有的阶级内涵。
至战国时代,宗法制度演变后的结局就是:由父权家长制大家族转变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家庭,由以宗族为本位的社会形态变为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形态;宗法政治等级已被封建社会等级所代替,广占田地的身为地主,占地少或无地者就是百姓庶民。同姓、异姓、庶姓已逐渐同化,家庭内实行一夫一妻制;社会等级的分辨普遍不复以族类作为尊卑贵贱的标准。孔子曾在《论语》以“有教无类”[42]作为他办学的宗旨。按“类”即“族”,无“类”即无“族”也,则孔子之语简要地说明了春秋战国之际宗旗单位的消失,故他可以不问族界来教授弟子。基于这个前提,“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于文”[43]。但“论地望者,则以贵贱为主,然贵贱升沉,何常之有”?[44]由此形成了“家无常姓”[45]的社会新特征。当时是“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46]与姓明其祖之所出,氏别其贵贱的姓氏旧制度比较,已是大相径庭了。
在春秋时代的姓氏制度中,庶人既无姓,亦不言氏,仅能有名。历经宗法制度的变化后,庶人阶层亦因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在“家无常姓”的新条件下,由原来示其地位低下的“名”,变为了个人独有的“名”,并与新近获得的“姓”,形成了战国时代新的姓氏制度。这种新形成的姓氏制度,是新社会形态下家庭或个人的代称,多称姓与名,称氏的现象则已基本上消失或趋于减少;而最常见的却是众多纷繁的氏,亦已融合在新形成的百姓之中。
这时的百姓一词,早已不是百官代称。所谓“百”者,言其多也。《孝经·天子章》云: “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孔疏曰:“百姓,谓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举其多也……天下兆庶也。”那么,在战国时代人人皆有的“百姓”之中,当有许多由氏转化而来的姓。氏是宗法制度下各支庶小族的代称。这些氏在春秋末叶激烈的社会变化中,不是失姓灭亡了,就是溃散破坏了。而春秋中后期县制的建立,各卿大夫对于新夺得的土地巴不再进行赐封而分立其氏,这样,各宗族下的氏已不可能再具备有发生、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那些宗族或家族的先后破坏,使流离失所的宗族成员已无条件辨其祖姓,明其祖之所出,只好以各自原来所有的氏改称为姓。这就是说,贵族的子孙后裔在姓的作用丧失后,他们亦可以自称为他人的始祖正姓,从而使姓具有了从较为单一向纷繁众多发展的趋势,原来以表贵贱的氏也就变成了普通一姓。与上述姓的变化过程结合起来,这就在一个普遍广泛的基础上,改变了春秋时代的姓氏制度。《淮南子·览冥训》记载:“七国异族,……兼国有地。”高诱注云;“齐姓田,楚姓芊,燕姓姚,赵姓赵,韩姓韩,魏姓魏,秦姓赢,故异族也。”在这里,刘安与高诱所言的“异族”,实则为异姓的大国。田、赵、韩、魏,原皆以所食邑为氏,现言齐姓田、赵姓赵、韩姓韩、魏姓魏,又皆以氏为姓。名称异族,实则异姓,形成了战国时期新的姓氏制度发展的新阶段。至于楚姓芊、燕姓姚、秦姓赢,也都是以国姓为姓,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于秦始皇则日姓赵氏,而不说姓赢,足以证明秦赢姓此时已成为百姓中的一姓。顾炎武以为:如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而五帝以来之姓亡矣”[47]。征诸史实,知此绝非虚语。西周春秋时期具有尊祖敬宗、别其贵贱的姓氏制度,已变为战国时代以氏为姓、以名独有,仅为家庭或个人代称的姓氏制度,并以其独特的变化过程丰富和充实了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演变的内容。
注:
[1][2][6][10][11][43][44] 郑樵:《通志·氏族略序》。
[3]《辞海》“姓”字条引《通鉴外纪注》。
[4]《左传·桓公二年》。
[5]《盂鼎铭》。
[7][18][20]《国语·晋语四》。
[8]《荀子·礼论》。
[9][12][14][15]顾炎武, 《日知录》卷二十三,“氏族”条。
[13][16]《左传·隐公八年》。
[17]《礼记·郊特牲》。
[19]《左传·昭公六年》。
[21]《左传·定公九年》载:“分鲁公……殷民六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殷民为子姓,此处,一姓之下有六族,分为宗氏和分族,实际上就是一姓之下有同宗和同族的另一种说法。
[22]《礼记·大传》云:“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
[23][25]《礼记·丧服小记》。该书中所反映的宗法制度,多为儒家七十子后学所为,虽混杂了后世的某些情况,但还是保留了不少关于春秋时代宗法制度的史料。其中关于“五世则迁之宗”和“百世不迁之宗”的记载,虽不一定就是五世则迁,百世不迁,但也反映了大小宗形成时的一种现象。
[24][26]《礼记·大传》。
[27]《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28]《国语·楚语下》。
[29]《尚书·尧典》。
[30][31]《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32]《左传·昭公元年》。
[33]《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34]杜佑《通典·礼二十》。
[35][36]《管子·权修》。
[37]《墨子·辞过》。
[38]《墨子•非命上》。
[39]《礼记·王制》。
[40]《慎子·逸文》.
[41]《管子·形势》。
[42]《论语·卫灵公》。
[45]《管子·法禁》,
[46]《孟子·尽心下》。
[47]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 “姓”条。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学报》作者:李向平
责任编辑:M005文章来源:印象河南网
相关信息
著名人物
没有记录!
精彩展示
没有记录!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