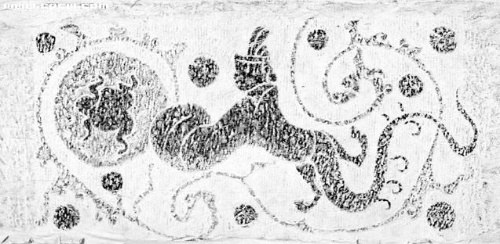-
没有记录!
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
2013/10/22 17:15:43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1)
秦灭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此后两千多年中,县始终是封建政权的基层单位,到清代,全国有1591个县。但清朝灭亡百年之后的今天,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曾经是各地最豪华、最醒目建筑的县衙竟然难觅踪影,这,从一个侧面见证了百年中国沧海桑田般的巨变。地处伏牛山南麓的内乡县,却把县衙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北京的专家们千里迢迢赶到这偏远小县,在这里打量着历史的背影,把这座不再有县官、不再有衙役的衙门,誉为“神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盛名之下,各色人等纷至沓来,想从这个窗口回望我们陌生而又熟悉的县衙,品味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官文化。
大门:兽头门环狰狞可怖
冬日的早晨,记者站在了大名鼎鼎的内乡县衙门口。县衙坐北朝南,古色古香,庭院深深,飞檐翘角的房屋层层叠叠,高低错落。清晨的太阳从东边照过来,向阳的屋脊上洒满了温暖的阳光,而背阴的地方青砖灰瓦地依然幽暗阴冷。明暗冷暖相互映衬,构成一幅很古典的、立体感极强的画面。
说起县衙,真不算陌生,古代没有乡一级政权机构,县衙是最接近黎民百姓的政府机关。在《七品芝麻官》、《十五贯》、《卷席筒》、《苏三起解》等影视戏剧中,见识过不少大老爷升堂问案的场面,所以站在县衙门口,我有几分亲切感,也有几分好奇心。
或许是因为我来得太早了,衙门口行人寥寥,喊冤鼓旁边,工作人员老王静静地清扫着地面。喊冤鼓被栅栏圈着,完全成了景观,我很想敲几下找找感觉,可踮着脚伸长了胳膊也够不着。老王过来拦住我:“这鼓不能随便敲的,过去没事乱敲要挨板子的。”弃了大鼓,我拿出手机,联系“衙门”里现如今的“官儿”———县衙博物馆副馆长徐新华,热情的徐馆长马上“摆驾出迎”。老徐是这个博物馆最早的倡建者之一,对县衙潜心研究多年。
衙门衙门,一衙之门先要看个仔细。县衙大门面阔三间,中间是明间过道,黑漆大门上,一个狰狞的兽头门环格外引人注目,据说各级衙门的大门上都有这样一个门环,就连故宫龙头朱漆大门上的兽头门环也同样狰狞可怖。兽头不美也不祥和,古代大大小小的官儿为什么格外偏爱这“动物凶猛”?徐新华说,实际上,衙门的“衙”通牙齿的“牙”,原意是指带有獠牙的门。在尚武的唐朝,衙门和牙门通用,而到了斯文的宋朝,人们逐渐不知道牙门为何物了,但门上狰狞的兽头却保留了下来。在古代,衙门是官府和权势的象征,狰狞的兽头体现了政权的强制性特征,说白了,就是用这个吓唬老百姓,制造森严压抑的气氛,让老百姓望而生畏。门房的东间前置喊冤鼓,供百姓击鼓鸣冤之用;西间前有两通石碑,分别刻着“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字样。越诉就是越级告状的意思,在古代这是影响县官政绩的事儿,所以大老爷在衙门口立下石碑,明文规定越诉要打50下屁股。
古代有俗话说:“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当时人们在走进衙门时总是很犹豫,这里是人们不得不依靠的国家机构,可里面又隐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黑暗和龌龊。别的不说,就是打板子时这板子的轻重差别可就大了。有记载说,在内乡县衙大堂上,时常有人被板子活活打死。过去人说“天下衙门深似海”,不光说的是衙门规模大房子多,更是说里面人精多,门道多,窍门多。
现如今的内乡县衙也是“无钱别进来”。因为这是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县衙,又是全国第一家衙门博物馆,进这个门要30元钱的门票。即便如此,这里还是人流不断,除去手持各种“条子”免费的,博物馆每年的门票收入还有一二百万元,在内乡这样的山区县,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仪门:礼仪之门规矩繁多
在内乡县衙走了一圈,最让我感到别扭的,是仪门;最让我庆幸没生在古代的,是大堂。
在县衙转悠,明显感觉到门多,过一道门又一道门,让人感叹庭院深深深几许。仪门是进了衙门后的第二道正门,这个建筑没别的用途,唯一的用途就是在大门和大堂之间多设一道门。
仪门,取“有仪可象”之义,是一道礼仪之门。门修得很宽敞,但好好的门平时紧闭着,不让人走。从此经过要走两边低矮的便门,并且两边的便门很不相同。西侧的便门称“鬼门”,也叫“死门”。“死门”平时关闭不开,只有在处决死刑犯前,才打开这个门,把死刑犯从这个门里拉出去行刑。因此旧时处决犯人也叫“出西门”,有上西天之意。东侧的便门称“人门”,也叫“生门”,这才是供人们日常出入的。在一年中,宽敞的仪门一般会开几次,比如逢着新官到任,或迎接同级、上级官员来访,县官就会下令大开仪门,自己也整冠出迎至仪门之外,大门以里,宾主从仪门而入(宾走西阶,主走东阶)。大堂如有重大庆典、礼仪活动或审理重大案件时也大开仪门,让百姓人等从中门而入,到大堂前参加庆典或观看县官审案。
听着介绍,我不禁感叹古人的规矩太多。县衙博物馆专门研究官衙文化的刘鹏九先生笑了:“细说起来规矩才多呢!你们年轻点的才不耐烦呢!”刘先生说,下级官员初次拜见上级官员要身着公服,从仪门东侧的便门进来,到长官面前要先将写有自己职衔、履历的名柬交上去,口称“卑职给大人请安”,行半跪礼。人家请就坐,还要谢座。就坐后,侧身面向“领导”,取半坐姿势,回答领导第一句话要起立作答,等领导示意坐下再就坐。一般谈话要结束的时候,侍者会端茶过来,但这茶千万不能喝,这是领导表示“你该走了”,即所谓“端茶送客”,这时不立马告退的都是傻子。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在清代的官场,这句话可真是一点不夸张。
大堂:刑具多多气氛森严
进了县衙大门,百米长的青石甬道穿过仪门直通大堂。大堂、二堂、三堂是县衙中轴线上的三大主体建筑,都建在高高的台基上,显得格外高大巍峨。其中大堂是整个衙门的中心建筑,最为壮观。大堂面阔五间,高11米多,建筑面积248平方米。大堂上方悬挂着“内乡县正堂”行楷金字匾额,堂前粗大的黑漆廊柱上有抱柱金联,上联是“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下联是“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知县掌握着一县的行政、立法、司法大权,这幅清代名联是大权在握、缺少制约的官员对自己的告诫。
大堂是知县发布政令、举行重大典礼、公开审理案件的地方,也是我们最为熟悉、在电视上看得最多的地方。内乡县衙大堂中央有一暖阁,是为知县审案设的公堂,内有三尺公案,上面放着惊堂木、文房四宝及红绿头案签。红头签为刑签,是下令动刑的;绿头签为捕签,是下令捕人的。当这签掷地有声的时候,便意味着一项重大案件正在审理的过程之中,马上就有人要皮开肉绽或被捉拿归案了。看看内乡县衙大堂的架势,或许能让我们感觉到古代官衙的严刑峻法。
暖阁正面屏风上绘着海水朝日图,寓意是为官者要清似海水,明如日月。再上头,照例有“明镜高悬”的匾。
暖阁前地坪上保留有两块青石板,东为原告石,西为被告石。两块石板上现在留有四个明显的跪坑,那是古人拿膝盖磨出来的。暖阁外两侧分别摆放着堂鼓、仪仗及刑具。东侧的刑具架上,摆着10多根黑红各半的水火棍,据说黑色象征水,红色象征火,寓意是罪犯的行为和国家的法律犹如水火互不相容。细看起来这些刑具很有讲究,有比较细的竹板,有粗大的木板,木板又有宽的、窄的和四棱子的,打起人来自然轻重大不相同。
据介绍,古代司法的主导思想是主张息讼,不主张打官司,所以有“入门三分罪”的说法,原告、被告都要长跪在坚硬的石板上,都要吃板子。受刑时男女不同,打男人是放翻在厚实的椿木凳上打屁股(据说打屁股是大唐天子李世民发明的,唐以前刑罚没固定部位,常打在腰背上,把人当场打死。李世民看到一张针灸图,发现腰背上穴位很多,而屁股上穴位很少,于是开恩下了圣旨,从此公堂上打屁股就成了定例);打女子则打在手掌上。
相比起来,西侧的刑具更可怕,墙根搁着夹棍,墙上挂着拶子。夹棍由三根木头做成,俗称“三木之刑”,是在审理人命案或者其他重案时,对证据确凿而拒不认罪的男性人犯使用的。据说上了夹棍疼痛难忍,手上加点劲就会夹断腿骨。拶子是为女犯人准备的,是专夹女人手指的刑具,也能让人痛彻骨髓。古代男人劳动主要靠腿,女人劳动主要靠手,所以夹棍和拶子这样的刑具破坏的都是人的劳动能力。即便是在残酷的古代,使用这样的刑具也必须禀告上级,验明烙印,并且限定在一次案件中对同一个犯人使用不得超过两次,否则就按酷刑逼供论处。
审案时,堂役击堂鼓三声,三班衙役两厢伺立,齐声高叫升堂,知县身着官服从暖阁东门进来,坐上大堂,然后原告被告被带上来,分别在大堂的原告石和被告石上跪下。退堂时也击鼓三声,叫做退堂鼓。退堂鼓成为日常生活用语,可见衙门文化的影响。
明清两代,知县很讲究大堂办事,为的是能“日与百姓相见”,加强他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和政治影响。对某些“不逞之徒”要“坐大堂对众杖之”,甚至“示以不测之威”,以惩一儆百,教育多数百姓,由此可见大堂的重要作用。
大堂后,还有二堂三堂等主体建筑。二堂是知县预审、初审和调处一般案件的地方。知县在此恩威并施,对当事人进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伦理思想教育,通过调解,征得双方同意,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目的。
三堂是知县日常办公、接待上级官员和商议政事的地方,一些涉及机密和不宜公开的隐私案件也在此审理。三堂的内部格局与大堂、二堂迥然不同,东边两间为接待室,西边两间为知县的起居室和更衣室。三堂左右两边是东西花厅院,是知县及其眷属居住的地方。后面为县衙的后花园,供知县赏心悦目、陶冶性情。
(2)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全国各地的衙门荡然无存了,可对于古代衙门黑暗的这种嘲讽,我们至今耳熟能详。封建时代的吏治时好时坏,但历朝历代的贪官污吏都不在少数。中国人坚信“有理走遍天下”,可就是到了衙门口的时候信心就不足了,古代大大小小的衙门到底怎么了?仔细看看内乡县衙或许能明白点什么。
“邑令催科无去处,班头衙役俱逃亡。”著名史学家史树青先生这两句诗我早就看过,原来觉得很是风趣,但到了他所吟咏的地方,才感觉到一种咏古之幽情。百年前,按照古代的作息时间,这个时候衙门里上上下下都该忙碌起来了,可现在眼前既没有挎腰刀的捕快、扛水火棍的衙役来回穿梭,也没有留长辫穿长袍表情忐忑的围观百姓,更没有喊冤鼓骤然敲响的悲愤和板子落下时的凄厉呼号……历史已经远去,往日不会重现,旧日的喧哗已经被现如今的宁静所代替。衙门不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县官和衙役“俱逃亡”,空空的院落成了一个供人观赏的“标本”。
三班吃陋规 六房收黑钱
内乡县衙长方形的大院子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四合院,这些四合院各自功能不同。仪门东侧的一个四合院,是皂、壮、快三班衙役值班的地方。皂班值堂役,负责站堂;壮班做力差,负责内勤;快班做缉捕,负责抓人。这些人统称为衙役,是古代最基层的“执法人员”,跟老百姓接触最多,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衙门的“形象”。
进了仪门,两侧分列着吏、户、礼、兵、刑、工六房。这六房与中央政府的六部相对应,内乡县衙博物馆副馆长徐新华通俗地解释说,吏房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户房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局加民政局,礼房相当于教育局,兵房则是武装部,刑房相当于公安局加司法局,工房则是城建局和水利局。每房有书吏2~3人。
别小看了三班六房,《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打虎英雄武松、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等,在上梁山前都是在县衙的三班六房上班。
从现存的建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古代一个县的行政机构基本都集中在了县衙,全部行政管理人员大约有100多人。依清代官制,县令为正七品,县令以下,有八品、九品的县丞、主簿、巡检、教谕以及一些不入流的官。但根据制度,全县“吃皇粮”的朝廷命官只有十来个人,其他职能部门如三班、六房等吏、役都无品级,不在官员之列。
六房的书吏大多读过书。他们大都是科场失意后,通过招募考试成为吏员的。书吏们是衙门的文职办事员,没有俸禄,合法的收入是很少的纸笔费、抄写费和饭食费。知县是一县之尊,还有县丞和主簿辅佐,但他们都是外地人,对本地情况不熟悉,也不可能胜任衙门内的全部事务。在衙门中真正办事的是这些书吏,他们承揽了衙门的全部事务,因此获得了权力,所以有“清朝与胥吏共天下”的说法。
衙役们享受国家“工食银”,每年六两或二三两不等。但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大清律例》把他们贬为贱籍,其子孙三代不得入仕做官。很多家族规定严禁其子孙充当衙役。
衙门里有大批这种手中握有权力而心理很不平衡的人,于是“吃陋规、收黑钱”成为衙门公开的秘密。所谓陋规,是历来相沿的不成文规矩,不合理不合法,但大家习以为常。按照清朝有关规定,六房书吏任职不得超过五年,但实际上很多书吏世代相传,他们对衙门内情况极为熟悉,营私舞弊很有一套,处处变着法盘剥百姓。对于进衙门打官司的百姓,衙役和书吏们用各种招数敲诈勒索。高高在上的县官对此也很清楚,但却无法根治,“任凭官清如水,无奈吏滑似油”,说的就是衙门的这种弊端。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积弊多多的衙门如同陷阱,老百姓一旦进来,就很难全身而退。有一首《息讼歌》曾广为流传,专说衙门中人如何“索钱有方”:
“听人教唆到衙前,告也要钱,诉也要钱。差人奉票有逢签,锁也要钱,开也要钱。地邻干证车马连,茶也要钱,酒也要钱。三班丁书最难言,审也要钱,和也要钱。自古官廉吏不廉,打也要钱,抄也要钱。”
千里去做官 为的银子钱
《十五贯》中的胡来胡知县有段很精彩的唱词:“两个老婆来告状,我一人罚她俩鸡蛋;两个铁匠来告状,我一人罚他两张镰。”《窦娥冤》中,楚州太守出场白就是:“我做官的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来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开庭审问时,太守见张驴儿跪下,竟然也急忙下跪。下属说:“他是告状的,怎生跪他?”太守答:“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戏剧是夸张的,这样不要一点体面的贪官儿可能并不多见。衙门里也出了不少好官,戏剧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唐成不用说,放浪形骸的郑板桥当了县官,曾做诗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其关心民间疾苦之情殷殷。当然,极好和极坏的官儿都是少数。封建时代官场广为流传的“千里去做官,为的银子钱”(另一个版本是“千里去做官,为的吃和穿”),恐怕道出了大部分官员真实的心态。
古代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做官必须到离自己家乡500里以外的地方去,所以元明清三代内乡的几百个县官没有一个是本地人。离开家乡几百里甚至千里之遥去做官,目的是谋得终身吃穿,所以才会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有人算过一笔账,知府每年的俸禄为105两,养廉银每年4000多两,三年的合法收入是12300多两,一位清正廉洁的知府,怎么会挣到10万两雪花银呢?原来还有名目繁多的“敬”,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过年过节、婚丧嫁娶还有拜礼、贺礼等,算下来每年可得数万两,这样一个任期下来,十万银子就到手了。当时人们对官吏廉与不廉有这样的区分标准:“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
为了使官员清廉,清朝独创了养廉银制度。当时官员的俸禄很低,七品官年薪45两银子,每月合3两多。按当时一般官吏的生活标准,3两多银子只够五六天的花费。于是地方官在收税时普遍加收所谓“火耗”,来增加自己的收入。雍正皇帝把这些“火耗”全部收归国有,然后再从中拿出一部分做养廉银,把官员的这部分收入合法化。当时县官的养廉银在每年1000两左右。但养廉银也不能遏止贪污索贿之风。
清朝的官员中,还有不少是捐纳得的官———根据当时的制度,士民向国家捐资纳粟,就可以取得官职。皇帝通过捐纳来增加国家收入。捐纳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最早出现在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1年)。到西汉时,捐纳已经形成制度,但最高只能买到相当于县令的官职。东汉灵帝卖官明码标价,张榜公布,现钱交易者还可以优惠。此后历代都有卖官之举。到清代,捐纳风更盛,康熙时出银4000两可捐一知县,以至全国捐纳知县达500多人。道光时捐一知县的价码跌到999两。按照捐纳制度,士民不仅可以捐官,而且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及穿官服的待遇。出钱捐官的人大都是“将本求利”,当上官后很少有不鱼肉百姓的,他们中饱私囊,残民害政,更造成衙门的严重腐败。
捐纳知县手下的师爷,往往都是知县借贷金店银号的银两时,金店银号安插的人,是捐官“股份公司”的“股东代表”。这种人惟利是图,最会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知县明知也不敢加以阻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