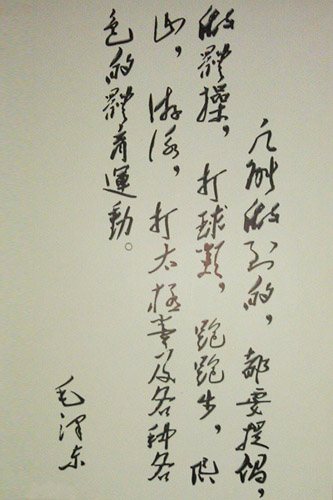-
没有记录!
“不似官窑,胜似官窑——当阳峪窑”系列之二 千劫千问当阳峪(2)
2014/2/17 14:57:50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焦先生边骑边讲,记者边看边问,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披荆上高,斩棘下低,看瓷窑遗址,观窑洞古房,如此这般,总算初步明白了一些东西——其实还是搞不清山谷里的东西南北。
寺河、西河(河西、河东两条沟合流后称西河)、东河3条河沟约略自西向东,汇入约略自北而南的瓮涧河(焦先生说:你千万别把东西南北当回事儿,这只是我们村里的叫法);在4条河5条沟中,寺河、西河(河西、河东)、瓮涧河皆有古窑遗址与瓷片堆积,东河无窑无瓷,只有煤炭;其中寺河之北坐落着圆融寺,当阳峪村在河西、河东与河东、东河夹峙的山丘上。而寺河、西河、东河夹峙的丘冈,宽在200~400米之间——这约略就是当阳峪瓷窑遗址的架构。
卡尔贝尔先生所称的“瓷谷”,当是“河东”;他的“瓷谷”,只是揭开了当阳峪窑的冰山一角。
抛却“瓷谷”
“现在的当阳峪村,不是从前的当阳峪村。”当阳峪村党支部副书记郭玉良说,“过去,河西、河东、寺河3条沟里都是当阳峪村村民,住的都是窑洞,下了雨河水一涨,就往窑洞里灌水,直接威胁着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984年新农村建设,才搬到了河西、河东、东河夹峙的山冈上,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当阳峪村。”
“村民从窑洞里出来了,盗贼进去了,他们租窑洞,挖古窑——
窑洞两旁,都是古窑,他们在窑洞里,都把活干了。”焦作市文物考古队前队长杨贵金先生说,“有的盗贼刚起步,没钱租窑洞,就在夜间干——2000多名村民顿然搬离3条偌大的‘瓷谷’,‘瓷谷’失去往日的热闹,死一般的沉寂,那盗贼不是想干啥就干啥了?!”
1990年前后的这次盗掘,对当阳峪窑是一次致命的毁灭。
“好在在此之际,焦作兴起了一批热爱当阳峪窑的收藏家。”杨贵金先生说,“以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此次盗掘出来的东西,包括好的瓷片,现在大都还在焦作。收藏者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出手自己手里的东西。好的东西,也大多留在了焦作。”
出现这一“景象”,当然与中国经济崛起密切相关,甚至盗掘与收藏,也是互为因果的。
1951年,陈万里先生曾经感叹:“可是到今天,要想见到几件真实的物品,极不容易,因为有好些宝贵的材料,都被帝国主义者盗去了。”——其实帝国主义者盗去,与中国当时的境况,何尝不是互为因果。
司瓦洛、卡尔贝尔“盗去”的,也许不乏精品;但在偌大的当阳峪窑遗址面前,他们“盗去”的不过是九牛一毛。
“一毛”撬动了整个西方世界乃至日本对当阳峪窑的研究,乃至某些收藏家的狼子野心;当然,也撬动起北京、上海等地古玩界对当阳峪窑的觊觎——很多人其意甚至不在收藏,而在把东西倒到国外。
1934年的中国,内忧外患俱在;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京津失陷,中原失陷……
谈起刨古瓷的事儿,当阳峪村村民王有州先生说:
我家居住在当阳峪村,世代为农,1943年,我4岁,天灾人祸大荒年,家里十几口人都给饿死了,就剩下伯父、父亲、哥哥与我,逃荒要饭度日如年。伯父、父亲讲,村里人迫于生计,到地里挖古瓷、瓷片卖。听说有人卖过一个透花瓷瓶(绞胎瓷瓶),三十大洋;人家转卖到北京,听说就五十大洋了。据说村里的韩清和在家里刨出了透花瓷碗,两个好的、一个烂的,卖到上海,好的每个二十大洋,烂的那个还卖了十个大洋。
都说为挖古瓷,1949年前,当阳峪的土地就被翻了个底朝天——只要能让百姓活命,就是翻它1000个底朝天,有何不可?!
其实,地里的东西也不是谁想刨就能刨出来的——不然,王老先生家也不会饿死十几口人了。
大地厚爱着当阳峪窑,1949年后还在不断发现精品瓷器,王先生说:
有个小孩儿在地里干活时,就刨出个透花瓷碗,焦作市博物馆收走了,奖给他10元钱。1973年前后,在村小学(校舍就是圆融寺),一个小学生铲地,铲出个罐,罐里两只白碗,还有小哨等小玩意儿。碗白得透明,跟玻璃似的,倒进水,从外边能看到水位;对着太阳看,里外透亮,真是好东西。当时老师孟战给收起来了,后来听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讲,省里来人,给拿走了。
两件事,都发生在小孩儿身上。
也许孩子还没有学会欺天骗地……□首席记者于茂世文图【原标题:“不似官窑,胜似官窑——当阳峪窑”系列之二 千劫千问当阳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