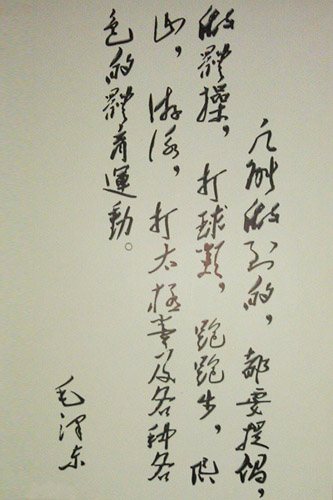-
没有记录!
肇始于巩义鼎盛于当阳 “当阳峪里说绞胎”系列之一
2014/2/17 14:45:44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古代中国是不折不扣的陶瓷之国,窑口如云,瓷种如林,可谓天下无敌。
古窑中,当阳峪窑是名窑;在古瓷中,绞胎瓷是名瓷。
修武县当阳峪古窑主要生产白瓷、青瓷(汝瓷、钧瓷)、紫定、白地黑花、刻划花、铁锈花、宋三彩等陶瓷,绞胎瓷产量很小,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不但产量小,且器物体量也小得可怜,几乎不见器高盈尺的绞胎,且大多是只有五六厘米之高的小盏小罐。
当时产量很小,而今存世更少,完整器皿仅五六十件。
无论在绞胎陶瓷创烧之地巩义窑遗址,还是在鼎盛之地当阳峪窑遗址,别说整器,今天就是想寻得一片绞胎残片,其难度,也近乎李白之攀援蜀道。
说起巩义窑,大家都知道其以唐三彩著称于世,乃至它是白瓷、青瓷、青花瓷等瓷种的主流源头,是唐代中国的一座“大成之窑”。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巩义窑创烧了绞胎陶瓷,也是中国绞胎陶瓷的发祥地。
“唐三彩是大唐梦华的一种标志性器物,自1905年发现以来,备受世人追捧。”巩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前所长席彦召先生说,“但是,在巩义窑遗址,最难寻求的却是绞胎陶瓷。可以说,在这儿,现在你连个绞胎残片标本都很难寻到了。”
巩义窑遗址如此,当阳峪窑遗址大体类似。
著名古陶瓷收藏家、北京睦明唐古瓷标本博物馆馆长白明先生在《片面之瓷•如梦似幻说绞胎——唐、宋绞胎瓷》中写道:“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的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曾到过当阳峪,对那里的‘文化遗存’甚为震惊,他谈道:当阳峪的绞胎瓷实在是绝妙,在这里连其碎片都能卖钱,乃当世之唯一……我也曾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过当阳峪窑,并见到过约有巴掌大小的一块宋代绞胎瓷方形小枕头的瓷片标本,只因当时的确是要价不菲,没舍得花钱,竟与之‘失之交臂’。所以,现在一想到我国陶瓷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以宋代绞胎瓷制作而成的‘杜家花枕’、‘裴家花枕’等稀世珍品,我就有一种要以头撞墙的‘冲动’,肠子都悔青了!”
“杜家花枕”现藏上海博物馆、“裴家花枕”现藏苏州博物馆,一般以为,这两件“花枕”,均是唐代巩义窑产品(其与白先生宋代之说,存有不恰)。
绞胎陶瓷创烧于唐代巩义窑,乃是将白、褐两种颜色的泥土(也有以三种不同颜色泥土者)一如卷“花卷馒头”一般,糅为一体,而后相绞、拉坯成型,抑或只是贴表在单色坯胎之表,施釉、煅烧,然后成器。于是,陶瓷器物上有了白、褐两色相间的纹理——由于绞糅方法不一,因此纹理变化多端,或如木纹、或如鸟羽、或如行云流水、或如团花草席,等等,形成独具一格的装饰效果,独步陶瓷之林,成为中国陶瓷大观园中唯一一种以胎体装饰陶瓷器物的艺术奇葩。
绞胎奇葩,缘何而盛开?因何而凋零?
绞胎奇葩,缘何重回当下人的视野?因何又在当阳峪窑故地焦作重生而“中兴”?
带着一系列疑问,记者下巩义、走修武,试图探求绞胎瓷的前世今生。
一寸绞胎一万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门初开,那时“万元户”一如当下的亿万富翁,怎么说都是“稀有动物”。
在巩义窑遗址上,一部分世代居住于此的百姓,因盗掘绞胎残瓷骤然成为“万元户”,亦因盗掘绞胎残瓷而为“阶下囚”。
“因为盗掘,抓捕了70多人,判了刑的也有10多个。”席彦召先生说,“当时一小块只有一平方寸大小的绞胎残片,当地百姓卖给坐镇收购的二道贩子,价格竟然是1万元人民币!”
一平方寸绞胎残片,二道贩子收购,1万元;走私出境,到底高到什么价位,只有天知地知倒卖者知道了。
“抓捕的、判刑的,都是当地百姓,警方连一个二道贩子都没抓到,怎么知道他们的交易价格?”席先生说,“据说,躲在幕后操盘的大买家是位澳大利亚人。”
在这个“食物链上”,最底层的盗掘者竟能分得1万元人民币,那么最后的大买家澳大利亚人,要购得一平方寸绞胎残片,想来也是不会低于1万美元的吧。
在地里挖,在公路上挖,乃至把自家的房子扒了,还是挖、挖、挖——尽管不好挖到,但归根结底,还是比安阳那位彩民独中3.6亿元大奖要容易一点儿的。
“缴获的绞胎标本,很少很少,到底出去了多少,没人知道。”席先生说,“这种事儿,不抓现行,谁会交代呀!再说都是单线联系,连一个二道贩子都没抓到,谁会洞悉全局情况!”
其实,绞胎陶瓷在1905年修筑陇海铁路时就有过发现,只是那时乃至此后很长一个时期,都把它归入“唐三彩”内。
“没人看懂,也没人注意,无论百姓还是学界,都把绞胎陶瓷当成唐三彩看待了。”席先生说。
巩义窑的绞胎陶瓷,几乎都施有绿色釉面、黄色釉面,其与三彩釉本是孪生兄弟,难怪难辨一时——尽管有的胎体呈色为褐,但其与花花绿绿的唐三彩看上去亦非常相似。再说,唐三彩几乎什么色彩都有,是“全彩”,倘若忽略胎体观察的话,误把绞胎陶瓷当做“三彩”陶瓷,亦在情理之中。
何况唐三彩红透世界,价位坚挺,绞胎难免“寄生”;何况绞胎藏在深闺人不识,既然能悠闲“寄生”,谁还会高喊“自立门户”。
经此大案后,席彦召先生开始整理数万片巩义窑陶瓷残片,从中细心甄别出数片绞胎残片。
“都是非常小的残片。”席先生说,“此次所得并综合其他绞胎标本,观察研究,发现唐代巩义窑生产的绞胎不仅有陶质的,也有瓷质的;不仅有半绞胎(表层贴面系绞胎而成,约占整个胎体的1/4~1/3,其余胎体为‘常胎’,不是绞胎),也有全绞胎,内外一致,我们叫它‘里外透’;有绞胎,也有绞釉,特别是绞釉,以前以为只有宋、元之际的当阳峪窑才生产,是绞胎陶瓷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现在看来绞胎与绞釉,当是同时诞生的;其源头,都在唐代巩义窑。”
绞釉陶瓷系以釉的自然流动,营造类似绞胎的装饰效果;鬼斧神工的绞釉陶瓷,其胎,则与一般陶瓷器皿毫无差别。
从目前发现的唐代绞胎陶瓷看,其器形,有枕、盘、碗乃至马,等等;其纹饰,有行云流水纹、木理纹、团花纹、菱形纹、莲花纹、太阳纹、圆圈纹、条状纹、花瓣纹、琥珀纹、五角纹、回形纹,等等。
唐代绞胎陶瓷乃至绞釉陶瓷,是诞生在巩义窑的一种陶瓷新工艺。
对于这一彰显古代窑工无穷智慧与创新精神的新的陶瓷品种缘何会在唐代诞生,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古人爱取瘿木为材制成各种器皿,器多花斑,纹理盘旋缠结,图案随意自然,不但文人喜欢瘿木器皿的高雅细致,就是王公贵族之间也以瘿木制品作为礼物相互赠送,今有瘿樽、瘿枕、瘿床等瘿木器物流传于世;另一种说法是,唐代工匠艺人们在制陶收工时,无意间将制各种陶时所用的胎、釉边角剩料搅拌在一起,制作成器,遂有绞胎陶瓷的诞生;还有一种说法是,绞胎陶瓷是受西方玻璃器皿的影响而诞生的,但在唐代丝绸之路各种商贸、交流的器物中,未见有与之类似的玻璃器皿出土或传世,况且西方玻璃中双色曲叠的花纹,早在几百年前就不再流行了;而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则是,绞胎陶瓷深受唐代犀皮漆器的影响,但唐代犀皮漆器纹有“片云、圆花、松鳞”等诸种不规则的大大小小斑块状图案,却没有类似绞胎陶瓷这样变化多端的丰富纹理。
在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交代。
其一,所谓“瘿”,就是“树瘤、树根”——病态的木头,也就是说,“瘿木”不是说一类树种,而是指树根部位结瘤、或树干结瘤部位的木材而已,因为“结瘤”,造成“瘿木”纹理特殊,效果奇异,颇具审美价值,令人爱怜。
其二,所谓“犀皮”工艺,就是与“犀牛皮”有关但也相去甚远,“犀皮”亦作“西皮”或“犀毗”,它是中国古代漆器制作中的一种装饰工艺,是将不同颜色的漆料堆涂在高低不平的器胎上,待漆料干透后,再经打磨,从而制造出色泽亮丽、光滑异常、自然生动、五色相叠的纹理装饰与艺术效果。
当然,无论在瘿木器皿还是“犀皮”工艺等的影响下而有绞胎陶瓷的说法,都只能归于当下的“猜想”。
釉、胎装饰齐维新
尽管只是“猜想”,但绞胎陶瓷作为一种器物,它的诞生与发展,不可能不受到其他器物的影响。
但是,再影响,也是不能把绞胎陶瓷诞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仿效他物的——外因只能是一个条件,内因才是事物产生与发展的基本因素。
再者,中国陶瓷的发展,岂能没有自身演进的轨迹呢?
关于陶瓷,现代考古学已经告诉了我们很多很多。但是,在神话乃至传说中,陶瓷的诞生地,在今日修武。
道光版《修武县志•沿革》云:“殷,畿内地,始名宁邑……《边志》云:读《仙释》谓之虞宁,是虞(虞舜,即舜)时亦名宁……旧志又以宁封子列《方伎》,则黄帝时,已有宁也。案:刘向《列仙传》,封子为黄帝陶正(主掌陶瓷的最高长官),后积火自燔(自焚),视其烬犹有余骨,人共葬之宁(地)北山中,故谓之宁封子。”
宁封子缘何“积火自燔”,在这儿,说得含糊其辞。
在道光版《修武县志•方外》中,此事说得相对清晰:“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之,以教封子。封子续火自焚,随烟上下。人视炉中,犹有骨,葬太行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