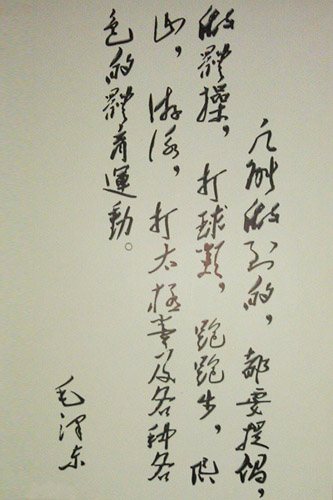-
没有记录!
“‘中天一柱’三圣塔”系列之一 “圣祚之碑”高唱女皇“革命有理”
2014/2/17 15:37:02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2008年年底,记者来到沁阳,为的是大清海疆(台湾)知府曹谨。河内县(今沁阳市)是曹谨故里,死后葬在河内县城南门之外,有墓在焉。
古塔在眼前忽隐忽现,却也始终没把它纳入心中。
探访曹谨遗迹,采访当地专家,不时提及这座古塔。
古塔名曰“三圣塔”。
不是唐塔,而是金塔。其外似唐,其内似宋,实乃金塔耳——建于金大定十一年,即公元1171年。
古塔在天宁寺遗址,天宁寺遗址现在被辟为沁阳市博物馆。
关于天宁寺,清道光五年版《河内县志》云:“大云寺在县城内东南隅,今名天宁寺。本隋文帝所置,名长寿寺。武后(武则天)改名大云寺。有(金)大定元年碑,后有塔,系大定十一年重建。”
除却县志上的这几次寺名更迭,天宁寺似乎迷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说起天宁寺,无论是当地专家还是当地百姓,都语焉不详。
但是,关于天宁寺三圣塔,“说道”不少:
有一个瑰异的传说——“金塔水井通东海”;
有一个千年的传奇——“三圣塔,地接天,垒塔不用刀砍砖”;
有一个美丽的故事——“砖塔抱木塔,小阁托大塔”……
关于“金塔水井通东海”,塔内有石刻“玉泉龙宫藏”;关于“三圣塔,地接天,垒塔不用刀砍砖”,塔的用砖,皆为量身定烧,自然不见刀之痕迹;关于“砖塔抱木塔,小阁托大塔”,因现在的金塔是重建之塔,早先的旧塔被包裹到了现在的新塔里面,自然也不难理解……
尽管传说与故事美丽瑰异,且为当下考古调查证实不虚,但沁阳人津津乐道的三圣塔,终究还是没能勾起我的太多兴趣——乃至没想前去一观一瞻。
一座金代的古塔,在河南,是稀松平常的——尽管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乃至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不想看它,就是不想写它:天宁寺模糊不清的寺史,让我犯难发憷;倘若只写塔的结构、艺术价值与建筑价值,不免艰涩,让读者难有兴趣。
尽管傲然挺立800余年的三圣塔作为“中天一柱”、沁阳的文化坐标,早已化入沁阳人的血脉,但它毕竟还只是积淀在沁阳人心中的一种骄傲。况且只是一种难以名状的骄傲,追问他们,说来说去,也就只有上面写过的那么几个传说与故事而已,几句话之后,就没下文了。
这样的三圣塔,尽管身为“国保”,《厚重河南》很难去写,天宁寺很难“昨日再现”。
不料,还是踏上了天宁寺遗址;不料,遗留在遗址的一通唐代《大云寺皇帝圣祚之碑》,给了我写下它的沧桑的些许信心……
“释教开革命之阶”而有女皇
不想观瞻三圣塔,只是不得不去。
因为沁阳之行,为的是海疆知府曹谨。在沁阳,有关曹谨的最为重要的文物——《曹谨墓志铭》,却嵌镶在沁阳市博物馆碑廊的新墙上。
沁阳市博物馆起于天宁寺故址,三圣塔就是博物馆院内。当然,30多米高的古塔,是院内最为“刺眼”的“庞然大物”。
新建的博物馆大门古色古香,看上去宛如一座古庙山门。
进得“山门”,惊见两厢古碑对峙。
如林夹峙的古碑尽头,站着高插云霄的三圣塔。
“山门”与三圣塔坐落在一条南北中轴线的两端。
两者相距约百米,中间无遮无拦,只有数处稍稍高出地面的房屋遗址——这是天宁寺大殿悄然留在沁阳大地的历史痕迹。
看到林立的古碑,心中顿生一种莫名的激动:死掉的天宁寺竟然留下这不死的三四十通古碑,古寺旧史,自可重建。
一盆冷水,当即浇下。
“古碑都是从其他地方迁移过来的,这儿是沁阳市博物馆《河内石苑》。”陪同记者采访的沁阳市文物局前局长李建兴先生说。
一时兴奋,竟然忘却自己的所在,不再是千年天宁寺,而是沁阳市博物馆了。
“在这几十通古碑、经幢中,只有《大云寺皇帝圣祚之碑》是天宁寺的。”李建兴先生补充说。
“怎么?大云寺碑?是不是武则天时期的古碑?”武则天与“大云”的关系,敏感而复杂,当为武周时代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
“是呀。《大云寺皇帝圣祚之碑》由‘太子中舍人、上柱国贾膺福撰文并书,睿祖康皇帝孙文林郎太原武尽礼勒上(就是勒石,‘勒上’乃应制之词)。”李建兴先生说。
贾膺福是武则天的重臣,曾负责佛经监译事务等,亦是武周时期的一代书家。武则天在神都洛阳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广三百尺……天册万岁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号为通天宫。四月朔日……改元为万岁通天。翌日,则天御通天宫……其年,铸铜为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豫州)鼎高一丈八尺……其八州(其他八州)鼎高一丈四尺……鼎上图写本州山川物产之像,仍令工书人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京等分题之……”贾膺福“善文,工书八分,笔法精妙,小楷尤工”,由他书丹的武周“修封禅坛记”,“永叔(欧阳修)、德父(赵明诚)皆称(修封禅坛记)精妙”,而康有为则称“《大云寺(碑)》亦有六朝遗意”。
武尽礼“笔法精劲,当时宜自名家”,是武则天的本家,是故自称“睿祖康皇帝孙”。
“睿祖康皇帝”何许人也?乃东周平王幼子姬武也。
姬武姓姬名武,武则天自认武姓源出姬武。
武则天登基后,立武氏七世先祖庙于洛阳。她自称武姓出自周朝王室,其先祖就是姬武。于是,周文王被追尊为“始祖文皇帝”,姬武被追尊为“睿祖康皇帝”。
为了宣示自己革李唐之命的正当性,武则天不但自认是周文王后裔,以与李唐皇室认在老子李耳名下相抗衡,以回答骆宾王在《为徐敬业讨武?檄》诟病于她的“地实寒微”,而且还在佛经里寻找女性可为皇帝的理论依据,这就是她为弥勒复生,以回答儒家说道的“牝鸡司晨”。《尚书·牧誓》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雌代雄鸣家尽,妇夺夫政国亡。
既然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找不到女人能当皇帝的理论依据,那么武则天只好把当时盛行的佛教作为她革李唐之命的理论工具。
就在她革命的前一年,一个白马寺和尚法明,向她献上了《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人世间)主”。
《大云经》曰:“即以女身,当王国土。”
《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今神皇王南阎浮提,一天下也。”
《大云经》曰:“女既承正,威伏天下,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违拒者。”
《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此明当今大臣及百姓等,尽忠孝者,即得子孙昌炽。”
关于《大云经》,向有此乃薛怀义、法明等伪造之经的说法。(《旧唐书·外戚传附薛怀义传》云:“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
1935年,陈寅恪先生依据敦煌本《大云经疏》,考出《大云经》乃薛怀义等取后凉昙无谶旧译《大方等大云经》,附以新疏而成,推翻了旧史所记武则天时有沙门伪撰《大云经》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