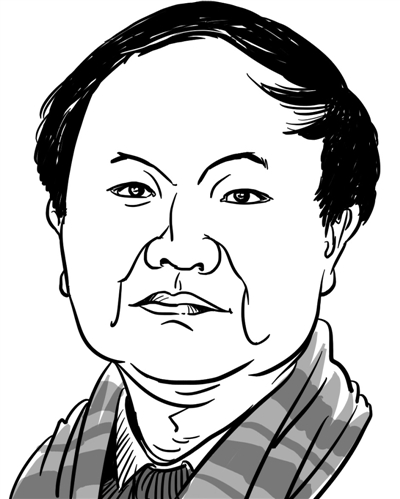-
没有记录!
刘庆邦:作家生来就是还泪的
2013/7/24 18:10:20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眼泪不是随便就能流出来的,每一个作家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还眼泪的。作品写完了,作家的眼泪也流干了。”刘庆邦来自河南农村,又经历过矿底下的生活磨砺。他自评“情感丰富,意志坚强,但情感却很脆弱”。
在他看来,天性的善良是成为作家的最根本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品中人物的眼泪其实也都是作家的眼泪。”
从1972年开始写作到现在,40年间,他创作了《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梅》《遍地月光》等7部长篇小说,《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30余种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这一篇篇、一部部,柔美或酷烈,都是在用眼泪和心血刻画着乡土与矿区人的生命姿态与情感。
刘庆邦边从书架上取下一部散文集送给记者,边解释道好多书自己也所剩不多,要留着自己看:“有时候我会被自己的作品感动得哭,被眼泪辣得读不下去……人们总希望看到那些浓烈的东西,其实那些浓烈之底隐藏的依然是朴素。”
230篇:成就“短篇王”
刘庆邦刚刚捧得首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虽然早已将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收入囊中,但被称为“短篇王”的他依然十分看重这个奖,“奖项的设置本身就体现了文学界对短篇小说的重视。”
众多学者将他的短篇当做“教科书”。林斤澜曾评价刘庆邦的小说“来自平民,出自平常,贵在平实,可谓三平有幸”。李敬泽在《鞋》中看到了小说悠远的文脉,它来自古典传统,经过沈从文、汪曾祺等现代作家的反复书写,同时还包含着自我审视和对古老乡土的回望。王安忆说,刘庆邦的小说总是有一个悬念,并且他也总不回避困难,有勇气也有力量开辟这一悬念,将“革命”进行到底……
记者仔细算了一下,刘庆邦已创作了230余篇短篇小说。“很多人对短篇现在的状况很担忧,但我一直是持乐观的态度。这是写作的一种生态,它会自然地调节和平衡。不管是短篇还是长篇,都是一种艺术的转换。”但他也很纳闷:都说现代人没有时间看书,但调查却显示长篇小说的销路更好。“出版社不愿意出短篇文集,总认为会赔钱,长篇就不至于。很多奖项也没设短篇奖。无论从舆论引导上还是市场反馈上,人们似乎都更看重长篇。”
在刘庆邦看来,短篇的艺术要求比较高,考量着一个作家的语言驾驭能力和想象力丰富程度,证明着文学艺术性的存在;而长篇满足的是人们看故事的愿望,这些故事很多是浅层次的,设置一个悬念吊起了人们的胃口,为了知道结果,人们会一个个故事地看下去。这是一种大众化的阅读,不是深度阅读,和看电视剧很相似,不用过脑子,看一个结果就完了。这种阅读方式也会使长篇小说的市场销售更好。
鲁迅先生写过中短篇,沈从文、萧红的小说大部分也都是中短篇,当代作家汪曾祺、莫言、刘恒最开始都是写短篇。“特别理解作家写长篇的愿望。我在写了很多短篇之后也会想写长篇。在写长篇的时候,会有一种放得很开、很过瘾、浩浩荡荡的感觉,这一点和短篇写作不太一样。但不能把长篇作为衡量作家的唯一标准,写短篇照样可以出大家。”
“像赛马一样,必须要先热热蹄子写短篇,再开始写长篇。但现在有一些新的作者直接写长篇,这不太合理。希望他们先从写短篇开始,这是一种对语言和结构的最基本训练。”
“写工人时,一定要超越工作本身”
刘庆邦在矿区生活了9年,“井下”构成了他创作动机的主要来源。长篇小说《断层》《红煤》,《神木》《走窑汉》等11部中篇和上百篇的短篇都在书写矿工生活。其中《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据此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
“关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这一转型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是他写作的定位。在《红煤》后记中他写了这样一句话:“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
刘庆邦不同意将工业题材作品单独归类,认为把工业生活从车间里脱离出来很重要,不能搞成车间文学。应更多地看到工人身上存在的社会性。工人承载着历史。但更深层地说是作家要注意到工人丰富的人的特点与情感。具体到某种工业,它会在工人身上打下一种烙印,体现出他的性格上的特点,不必过分强调他的行业性质。“在写工人的时侯,一定要超越他的工作本身,把他放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来考察。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情、人性,这样才能形成文学作品。我顶多写写地下的环境,从来不写工艺流程。因为这些东西对读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他举《神木》为例,虽然它反映的是矿工生活,但是矿井、煤矿只是一个舞台和载体。作品着重写的是人性的扭曲、变异、觉醒和复苏,但确实又反映了煤矿的特点,工业背景自然地表露出来,并未过分地强调。
刘庆邦觉得现在工业题材的淡化反而是文学的一种进步,是对艺术的一种回归。比如说写蓝领,写市民,虽没有贴上工人的标签,但它实际也是在写工人的生活,只是将它放到大的社会背景下写。
“我愿意到小煤矿去体验生活。因为小的煤矿还是有一定的原始性,工人之间在互相发生关系。人性还是比较容易表露出来。我可以从宿舍和食堂看出工人之间的关系,写出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故事。但是在大工业里工作的工人,下了班以后可能就直接回家了,人性人情都不表露出来,写的价值不大。”
前年刘庆邦在一个小煤矿的工人宿舍里住了十来天,去食堂排队买饭,去水很脏的小澡堂洗澡。工人们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持续写作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问题,这是一个态度问题。要保持平常心,把自己隐藏起来,放低姿态。”
好小说要看“含心量”
“好小说的判断得从文学的本质来看。小说的本质就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听从内心的召唤,投入自己的感情,直达人性的深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好不好要看小说中包含着作家多少真诚的心灵,也就是‘含心量’。其次就要看小说的情感是否饱满,能否打动读者。”刘庆邦将对于情感的衡量放在评判一本小说的中心位置上。“作家要忠于自己的所感所思,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情感美是刘庆邦作品美学的核心。他说,文学作品是审美的东西,情感之美应该是美的核心,是中心之美。任何门类的作品,包括文学、影视、曲艺等,都是为了表达人的情感的。这是不管什么时期都不会变的。感动并不是单指让人流泪,甚至恐惧、震惊等都是感情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感情的一种冲击。但是感情是一定要有的。当然还要有艺术上的形式:情节的完美、语言的味道、结构的合理等。
心灵化(含心量)、情感的饱满、情节、细节、语言这几个方面都要恰到好处,是他心目中好作品的标准。
“每个作家在生命深处都是悲凉的、悲痛的,生命就是个悲剧,作品都是表达作家脆弱的感情。真正好的作品,它应该是柔软的。”
他引用一种极端的说法:“哭泣乃灵气之谓也”,哭泣有几分,灵气就有几分。哭泣指的就是人的眼泪。因为作家的内心是善良的,敏感的,才能发现善良,才能对于“恶的东西”感受更强烈。
因为如此,“一个善良的人也许努力之后能成为作家,但是恶人永远成不了作家。”刘庆邦说,“天性的善良是成为作家的最根本的条件。”在他眼中作家的善良源于天性。作家具有悲悯情怀是因为他们提前看到了生命的尽头,认识到人生非常短暂和宝贵。于是,对待世界才会有一种包容和善意的态度。
“我认为文学和宗教之所以一直伴随着人类,是因为它们能够使人们产生悲悯情怀和善良的意识。”刘庆邦说。【原标题:刘庆邦:作家生来就是还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