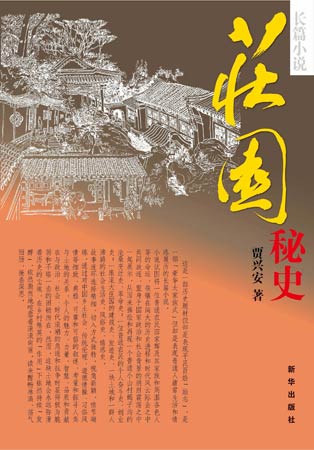-
没有记录!
- 1、袁世凯后人:大总统之孙
- 2、一代风雅李化龙
- 3、刘邦的家庭与出生的传说
- 4、周汝昌与张伯驹二三事
- 5、正骨巨子——郭维淮
- 6、陈胜的长处和短处
- 7、王天定摄影展开展
- 8、擒豹英雄97华诞郑州行:东方超人何广位
又一部命运之书,这一次确立的现实是改写“地主”
2013/7/16 16:18:50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比起《黄土青天》和《县长门》来,这部《庄园秘史》更像是信手拈来之作。这么说,丝毫也不意味着我看它容易,不以为得来不费工夫。套用兴安自己的话说,这叫“都不容易”。我一直关注兴安的创作,曾经写过四篇文章。借这个机会,回头梳理一下我的思路,我觉得对兴安的创作,也应该趁便加以全面梳理、总结,尽管我力有不逮。
早在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景物与一些人》读后,那时我说,兴安有自己的文学信念,只听命于自己,别的,爱谁谁。兴安尤其钟情“老家”,钟情“过去”,念念不忘童年的馈赠。记忆一旦被他唤起,就带到纸上,就漫步开来,让人觉着近乎“讲古”,却又见容于时代。我还说,他从容、兼容,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可写,他觉得该写什么,就写起来,不在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上同自己较劲,也不同别人较劲。在他看来,生活永远是可爱的,同时又是永远存在问题的,这就是他写作的理由与背景。
至今我依然确信,以上两点,有助于理解兴安的为人为文。一个作家的生命性质,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隐入文字的背后,不管文字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他的个人禀赋、气质与经历,总会显现。
当年从《陋乡苍黄》到《黄土青天》我也一再鼓吹。在《陋乡苍黄》研讨会上,我有一个发言,后来被一并归置到国家社科项目——《世纪之交:长篇小说与文化解读》一书中,因而到了《黄土青天》研讨会上,我就偷懒儿了,抱着书在会上念:
小说直面现实,语言浓重而鲜活,富于思辩色彩,结构严谨有气度,通篇一气呵成,描写了崇高的奉献,尤其是主人公为民请命的忧国忧民的使命感,是最近几年来农村题材小说中不多见的。
作者着力笔墨的主人公成为小说的巨人式人物,是当下体制中的包青天。然而从作者的创作本意来讲,这是一种符合现实主义的角色选择,落后的体制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被改革完毕,所以一位清官就仍是当下一个务实的现实选择。
随后,省“五个一工程奖”评奖,有机会重读《黄土青天》,我有一些新的想法,写了这样一个授奖词:
这是一部有血性的书,很好地继承了《红旗谱》的传统;这是一部写了许多问题的书,但不是问题小说,也不是官场小说,而是弘扬正气的主旋律作品;这是一部反映农村变革的教科书,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现实农村,具有充分的批判和认识价值;它创造性地、成功地塑造了新人物,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像王天生那样的当代英雄形象;从根本上说,它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它或许不是我们眼熟的“现实主义”,确是本质上的现实主义,它不是重述现实,而是确立了一个现实。
到了《县长门》,我写了《命名的真实与现实的确立》一文,我说《县长门》与《黄土青天》从气质上有一脉相承之处,集中体现于再次创造性地、成功地塑造了新人物,依然涉及到一些问题和官场,依然不是问题小说或官场小说,而是确立了又一个现实。兴安坚定地保持了只听命于自己的创作姿态,他就是他,他开创,从不复制。不复制别人,也不复制自我。他的创作,与其内在精神结构呼应得相当好。
那么这次我想说,《庄园秘史》与《黄土青天》与《县长门》从气质上依然有一脉相承之处,集中体现于再次创造性地、成功地塑造了新人物田家辉,确立了又一个现实:改写“地主”二字。
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庄园秘史》对地主尤其是地主成长史的关注、研究。这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
长篇小说读的是命运。我读《黄土青天》、《县长门》读出了“命运”,读《庄园秘史》,读出的还是“命运”。我知道《庄园秘史》是小说,是虚构,但我对它的真实背景深信不疑。
有人说,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历史变动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的巅峰,惟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这一观点,被许多人认同,我倒觉得在读了《庄园秘史》之后,应该有“例外”的感觉。起码,兴安笔下的地主,有别于现当代尤其是十七年文学中的任何一个地主形象。
兴安有着神圣使命感有着充沛的生命意向有着难得的清醒,他所书写的乱世危局,一个地主与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条血泪之路对城乡的连接……一地三个政府三个县长……国共与土匪的混杂……足以显示其对事实证据的掌握程度、对事实的理解程度和他对历史介入的动机,在我看来至少还原了部分历史真相,使我们对那段历史再次有了触目惊心的感觉,反思我们的视听、思想包括历史想像力的局限,坚定我们对历史真实的理解程度和判断立场:这是命运的历史,而且并不仅仅是已经过去了的历史……我想,只有理解了这些,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庄园秘史》独特品质的历史来源。
《庄园秘史》让我想起许多年前我在文安大郭庄,在老支书郭建华的带领下,我们用了许多天,走过大郭庄的每一块土地。有一天我对郭老说:“你们村当年肯定出过大地主!”他很惊诧,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是从这大片大片的肥沃的土地上看见的,我看见了历朝历代的财富尤其是土地的积聚,看见了智慧和血汗。郭老非常认同我的观点,尽管,他是当年的贫农团主席,从斗地主开始,他成为那个村庄的当家人。老支书说:“没有那些地主、富农,就没有今天这么大的大郭庄,没有农业学大寨,就没有今天这么富裕的大郭庄。”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大郭庄村南的“康庄大道”上散步,他突然拉住我的手说:“世上最长的是道路,路是走不完的,我是奔八十的人了,你们替大郭庄物色一个接班人吧。”后来我得知衡水作家李祝尧写长篇小说《世道》,让他去大郭庄采访,成就半部书。
《庄园秘史》还让我想起另外两件事,也与地主有关。
我的老家有过一个地主,姓吴,走四十里路不喝别人家的井水。据说他发家是十分偶然的,仅仅是有一年他家的椴麻卖了个好价钱。为了买地,他舍不得吃穿,长工吃干的,他喝稀的。最终,他还是被活活打死了。在斗争他时,说他富有的唯一实证是他有瓦房,还一条厚厚的棉裤,厚到往炕上那么一戳,可以立住不倒。那是他唯一的一条厚棉裤,为他的老寒腿准备的。吴家有五子,其中四个勤劳守业,抗战时都是英雄好汉,后来成了地主、富农,被批斗,家破人亡。另一个,吃喝嫖赌,片瓦不存,后来成为贫农,“文化大革命”中挨斗时他总是叫:“我可是地道的老贫农啊!”显得很委屈。
我在山西还结识一个老贫农,“文革”时曾登台诉苦。他说:“想当年老地主那个狠啊,让我们干活,他自己歇着,给我们吃小米干饭拌豆腐,他吃白面。哎,要说那会儿还能吃上小米干饭,现在连小米粥也喝不上了。”说着说着说跑了,他被赶下台,后来又被揪上台,跟着地主挨批。这些,在《庄园秘史》的“天上布满星”一章,更形象,更生动。
说起这些,是我觉得,《庄园秘史》的视角,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视角,揭示出许多东西,笔,探到了土地深处,触及土地的记忆,可以唤起人类共同的记忆,尤其可以调动熟悉这段历史的中国人。纵观全书,田家辉、郭子义、二臭等诸多人物,是戳得住的,是形象的。它触及了生活和生存,回应了历史。透过文字,可以看到命运:农民的命运,土地的命运,甚至革命的命运。这就决定了这部书总体上的成就,是又一部命运之书。
我个人是一直喜欢这一类文学的,有生命的投入,有精神的苏醒,有自我的发现和觉悟。但凡好的文学,基本上都是从这个路径上来的。文学的后面要有人,要戳得住,要有心,要摸的着,要有精神的挣扎和超越,这是文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摇动的价值向度。
我一上来就说,这部《庄园秘史》更像是信手拈来之作,其实我是要说,和《县长门》一样,正因为准备充分,才显得举重若轻。前几年兴安出过两部在我看来很重要的随笔集,一部是我前面提到的《都不容易》,一部是《村庄里的事物》。《都不容易》关涉兴安的胸襟气度、悲悯情怀。兴安的作品,对所有角色都是充满世俗同情的,正如曹雪芹对宝钗,对贾政,对刘姥姥,对老妈子,如惠特曼对黑奴,对妓女和逃兵。在《庄园秘史》中,世俗同情没有被世俗政治、道德所约束,使人物有了多重的乃至不可分重的性格,让蝎子沟那样一个原来冷酷无情、没有人味儿的地方,有了温暖,有了人味儿。而《村庄里的事物》中对移民与村落、民居、民谣、乡村老宅院、水井的关注,对于构建《庄园秘史》这样一个由经验、细节和材料所建构起来的物质外壳,非常有帮助,最终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灵魂容器。从挖黄豆、豆腐刀、打豆腐、腰带绳,到庄园的布局、砖雕、石刻、家具,在物质层面、在日常生活层面有着比较严密、精细的描写,大部分细节都经得住推敲,这在作品推进的过程中,大大提升了逻辑性、可信度和经验的真实性,使小说的精神和它的物质外壳融为一体,呈现出日子和事物的纹理。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关于细节处理,也有一点点瑕疵,将来再版的时候,建议兴安兄修订一下,一是有些东西要往细里抠一抠,再是在起承转合的“转”字上下功夫。有的硬伤,一定要改,举两个小例子:第4章36页,二臭说家里有山鸡蛋,是在1913年3月18日,那时节山鸡下蛋早了点,在燕山山鸡下蛋是在6月初,在太行山早半个月,在5月中旬;第11章106页,“向阳的坡面有一些果树,但都是野生的,村人谁摘了算谁的。”果树野生的少,除了核桃、栗子,苹果、梨、山楂、桃、杏、李子之类都需要嫁接,野生的不是果树,果木种子返祖,只可作为果树嫁接的父本。核桃、栗子可以直接种,要想提升品质,也需要嫁接。刘向东【原标题:又一部命运之书,这一次确立的现实是改写“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