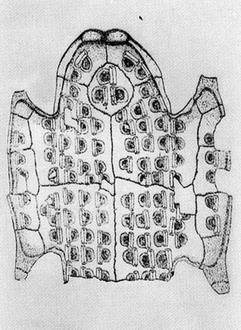精彩推荐
热点关注
专题推荐
-
没有记录!
热点排行
先秦两汉时期河图洛书的源流与嬗变
2013/6/24 10:52:01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千百年来,人们在论及中华文化的起源和代表性文化符号时,总是离不开河图洛书。然而,河图洛书的原始形态是怎样的,经历了哪些演变与改造,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却是众说纷纭,扑朔迷离。河图洛书的源流与嬗变,遂成为中国文化和思想史上讼而不决的一桩公案。概而言之,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原是一种应帝王受命的祥瑞和神物;至两汉以迄宋元,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需要下,人们对其作了种种推演、改造,“河图洛书”遂演变成“龙马负图,神龟贡书”的神话般的传说故事及图谶之说,并日益图式化和玄理化。河图洛书的嬗变不仅对于古代易学、儒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政局兴衰、朝代更替和人们的文化生活也产生了诸多影响。
祥瑞之兆: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说
先秦时代,《尚书》、《论语》、《易传》、《墨子》和《管子》等经典文献中都留下了有关河图洛书的记载。《尚书·顾命》中提及“河图”时说:“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这句话按照东汉郑玄的解释是说,陈列在东序的“大玉、夷玉、天球”,此“三者皆璞未见琢治,故不以礼”;对于“河图”,郑玄说是“器名之河图,图出于河水,帝王圣者所受”。据此可知,《顾命》篇中的河图是一种金石之类的国宝,作为祥瑞之兆由帝王所受,并无后世所谓“龙图出河”之义;《尚书》中,被后人传为与洛书有关的记载是《洪范》篇。然而据考证,《洪范》篇的产生是在周武王伐纣胜利之后,箕子向武王详细阐述洪范九畴,即治国的九种大法,亦与“神龟出洛”之说不同。可见,《尚书》中所记载的“河图”与“九畴”,与后人所理解的“河图”与“洛书”有很大的出入。
《论语》中有关河图的记载,即如《子罕》篇中所云:“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从字面来看,“凤鸟”是一种神鸟,可谓吉祥之物;而依《尚书》所说,“河图”是一种金玉之器,亦可谓国宝之物、吉祥之兆。孔子此时此刻深深地感到:凤鸟不再到来,河图也不再出现,那么,我的使命不也快要结束了吗?孔子立志行道而道不行,这段话当是其自感怀才不遇、生不逢时而发出的喟叹。
《易传》中涉及河图洛书的是《系辞上传》,“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句话是说,天生蓍龟等神物,圣人用它来创立卜筮的法则;天地出现日月四时之变化,圣人依据它而确立了阴阳观;河出龙图、洛出龟书之祥瑞神物,圣人取法它来创制“易”道原理。“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句中,“河图洛书”究竟指代什么?圣人依其所“则”的又是什么?前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联系全文来看,“河图洛书”指的仍然是蓍龟之类的祥瑞之物,圣人取法它来创制《易》卦,只有如此理解,才能把前后意思说得通。
《墨子》有曰:“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武王践功。”“绿”通“籙”,故“绿图”与符一样,亦为帝王受命之物。“乘黄”据考是一种神马之名。因此其意是说,周文王灭殷兴周是天命所归,故有“河出绿图,地出乘黄”之瑞兆,武王应天之命,终于伐纣成功。此外,在《管子·小匡》篇中,还提出“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等三祥之物,亦皆具祥瑞之义。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虽然具体形式尚有争议,但其作为一种圣王接受的祥瑞之物,大体是不会错的。这一时期有关河图洛书的记载还看不到后世的龙马、神龟、伏羲以及种种具体细节,尚带有原始图腾的象征意义。
神话传说与谶纬之学:两汉时代的河图洛书说
两汉时代的河图洛书说,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由先秦时代的内容简略的祥瑞义蕴,一变而为两汉时代“龙马负图,神龟贡书”的神话般的传说故事;再就是由西汉时期的神话传说,一变而为东汉时期的谶纬之学与河图洛书。
西汉时期,第一个演绎河图洛书神话故事的是名儒孔安国。孔安国对河图洛书的创意,是通过后人之口而流传的。他在《尚书正义》的《顾命》篇和《洪范》篇中,分别说:“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序。”综合孔颖达在《周易正义·系辞传》中所引孔安国的观点来看,孔安国对“河图洛书”的认识有两点:一是伏羲依河图以画八卦,大禹依洛书以定九畴;二是河图即是八卦,洛书即是九畴。这不仅把原本模糊的祥瑞之兆衍生出“龙马负图,神龟贡书”的具体情节,而且把其中的圣人具体地与伏羲、大禹等先贤联系起来,并演绎出其与八卦、洪范九畴的神秘联系,内容丰富、深刻得多。继孔安国之后,刘歆和班固对此进行了更多的阐发。如班固对河图洛书的一个创意,就是把“洛书”之文与洪范九畴捆绑在一起。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以史书的形式把《尚书·洪范》篇中的六十五字定为“洛书”本文的一种新说,并为伏羲、大禹的相关传说增添了可信度与合理性。
东汉时期还出现另外一种趋向,就是河图洛书已经演变发展成为有文字、成篇章的书籍,而且和谶纬之学融合在一起,名之曰图谶。这种变化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尤其是上层统治者的喜好密切相关的:“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后汉书·方术传》)所谓“谶”,“诡为隐语,预决吉凶”,是一种神秘的预言。它出现较早,秦初就出现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语,于是秦始皇就大修长城,严防匈奴(时人称之为胡),但结果是秦朝没有亡于匈奴,而是亡在秦二世胡亥手里,时人称此胡非彼胡。所谓“纬”,则是用神学观点来解释经义,并把此种解释假托于孔子的书。与《易经》、《诗经》、《书经》等“六经”相对应,有《易纬》、《诗纬》、《尚书纬》等所谓“六纬”。西汉末年后,社会动荡,危机重重,谶、纬合流,著书立说,编造预言风行一时。
谶纬之学达到高峰期,当在汉光武帝即位之后。光武帝刘秀是把河图洛书作为做皇帝的天命根据的第一人。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群臣上言,要求刘秀封禅,刘秀未允。两年之后,他在斋戒时读到《河图会昌符》中的“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乃令梁松等人重新根据“河图洛书”,向他说明有关封禅问题。梁松等查到了三十六条根据,奏请光武帝封禅。于是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刘秀登临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并刻石以记之。作为东汉开国皇帝的光武帝,一方面对于应运而起的图谶进行编纂修定,另一方面又亲临泰山搞封禅活动,宣扬皇权神授,这些做法使得河图洛书日益正统化和神圣化。如《后汉书·张衡传》所云:“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谶,兼附以妖言。”此后,明帝、章帝等沿袭其风,大搞图谶,河图洛书对当时儒学和整个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当时群臣向曹丕上劝进表时,亦纷纷援引《河图洛书》,如太史丞许芝表称:“伏惟殿下体尧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禅代,当汤武之期运,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图谶所载,昭然明白,天下学士所共见也”。“且《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效之。以为天文因人而变。至于《河》、《洛》之书,著于《洪范》,则殷、周效而用之矣”。接着,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郎等又奏称:“《河图洛书》,天命瑞应,人事协于天时,民言协于天叙。”后来此三人又率九卿上表云:“伏惟群臣内外前后章奏,所以陈叙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条《河》、《洛》之图书,据天地之瑞应”。正是从河图洛书中寻找到如此充足的依据,于是曹丕顺水推舟,择日告天,从汉献帝手中接过了禅位诏书。
谶纬之风盛行不仅使河图、洛书成为帝王接受天命的符瑞,而且更被作为政权正统的象征所在。刚上台的帝王,总想利用河图洛书中的谶纬迷信思想,来寻找他该做皇帝的理论根据。龙马负《图》出于河、玄龟背《书》出于洛,是谶纬文献中出现得最多的帝王受命神话和祀典。因此,谶纬中的河图洛书为数颇多,如《河图会昌符》、《河图合古篇》、《雒书甄曜度》等,据日本学者安居香山等统计,河图类纬书有43种,洛书类纬书有18种。其内容多就先秦时代有关河图洛书的只言片语,进行发挥甚至无限引申,穿凿附会,不仅有所谓龙马、神龟,且情节生动离奇,涉及伏羲、黄帝、唐尧、虞舜、周文王、秦始皇、汉高祖等帝王和先贤。这些神话和传说的流行从各地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所谓负图寺、龙马庙等遗迹、遗址中可见一斑。
总之,河图洛书作为一种祥瑞义蕴,龙马也好,神龟也好,凤鸟也好,地黄(神马名)也好,皆为吉祥之义(物)。正是由于两汉儒士迎合政局更替和时代需要,对其进行改造和推演,才逐步衍生出龙马负图和神龟贡书等具体内容,并作为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的《易经》和《尚书·洪范》的重要来源。这种变化造成河图洛书的神话色彩和正统意味日浓,并且开了后世河图洛书不断嬗变的源头。至宋代,河图洛书出现了又一次大的改变。北宋的陈抟、刘牧、王安石、苏轼,南宋的朱熹、蔡元定等名儒一改前人的解《易》方式,以“图十书九”等图式来解释《周易》的原理,出现了各种图式和图说,后人称之为图书学派。而北宋的欧阳修、程颐,南宋的薛季宣、林至等则主张疑古辨伪,求真信实,认为自汉至宋的所谓河图洛书皆为附会之作,不足为凭,后人称之为反图学派。双方针锋相对,对河图洛书的具体内涵、地位等争论不休,对理学、易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董延寿 史善刚)
责任编辑:C006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10-08-13
相关信息
没有记录!
著名人物
没有记录!
精彩展示
没有记录!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