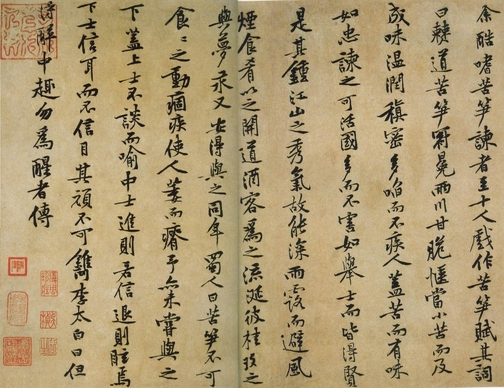-
没有记录!
林风眠水墨画的启示
2013/10/23 14:12:16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林风眠的水墨画是近现代中国水墨画现代化转型以及融合中西绘画取得卓越成就的一个重要范例。他的学画经历、艺术思想、绘画风格,伴随着时代的演进与变革,既给他带来了荣耀和成就,也让他遭遇了痛苦与凄凉。但林风眠一如既往地坚守着融合中西绘画的探索之路,他那丰富而传奇的人生经历也成为他艺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源泉。
作为中国现代水墨画的开拓者,林风眠的艺术思想和实践为后学开启了新的法门。就我个人的浅薄体会谈谈林风眠绘画的几点启示。
林风眠的水墨画拓展了原先对中国画传统认知的狭义界定。中国画的传统应由院体画、文人画、民间画三大部分组成,然而历代中国画传承多关注于院体画和文人画,对民间画却少有问津。或许因为古代从事中国画的多为士族贵胄,他们崇尚雅逸之风,耻于沾染画工的市井流俗气,故传统画脉中鲜有民间画迹的掺入,以致渐渐缺失了原始的勃勃生机与张力。张大千先生的画名饮誉海内外,他在中国画学上的贡献之一:即临摹、研究了民间画代表的敦煌壁画,并吸收变化到文人画的题材中来。同样林风眠在法国老师扬西斯教授的点拨下开始学习中国民间画之传统,如古陶瓷器物上的图案、线条等,这些元素在他作品中的运用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画讲求程式,程式也是区别于其他画种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画的演进是在程式的研习传承中寻求变化和发展,于此中国画学之文脉得以完好地承续下来。程式的运用关键在于“通变”,只有会通变方能“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倘若程式落于凡庸之手,则陈陈因袭,了无生机了。林氏学画以西学入手,有别于国学绘画之传统,他力主将中西绘画之高峰融于一体从而改良时代摒弃的传统画学。因此他既未涉足传统程式,自然也远离了程式的累赘,于是凭借自身的才学紧紧抓住了艺术的“感知”与“直觉”,讲求以特定的情感来注入或影响画面,这恰恰正是传统中国画因过度强调程式的经验而忽略了重要的另一面。
20世纪可谓中西文化交汇碰撞最为激烈的时代,中国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变革。黄宾虹、齐白石等前辈是以传统国学为基点融会古今与时代建树中国画,林风眠先生积极响应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坚持以西学的美术来改良国学的中国画,创作出了具有中国画情调的中西融合的水墨画。其标新立异的形式和雅逸孤傲的格调,为中国画当代性的探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他画面的内容、取景、构图、光色的处理以及用笔的方式都源于西画的学习而有别于传统经典的骨法用笔或经营位置,可是他的作品(除早年的现实主义题材外),主要是1950年代以后的作品,大多让观者感受到了充溢着浓郁的“诗性”特征。“诗性”的抒情是中国画特有的文化气质,林风眠将中国文化的这一基本特质有意无意地保留在了他的作品中,于是西方形质、东方情调的新水墨画由此诞生了。可见中国画家在其血脉中始终有着无法剔除的民族文化基因。他那种浓浓的乡愁、内心的无助与孤寂,正应和了古典诗词中迁客逐臣的情境。宋画《潇湘八景图》中之《平沙落雁》一幅,此中之“雁”隐喻了画者无辜被逐、去国怀乡的忧思,我想林氏画中的芦雁、秋鹜以及印象中的儿时山村,一定有着相似的寓意。林风眠绘画中的诗性隐喻之特质,成为了他现代水墨民族化的有力注脚,也许这是他又一伟大之处吧。
作为现代艺术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林风眠的绘画观点同样反映在他的艺术教育思想上。如果说同样是引入西画改造中国画的教学理念,徐悲鸿校长借用的是西方古典艺术的教学法则来转换创作现实主义题材的中国画作品,在他的体系中培养出了吴作人、蒋兆和等现实主义画家。而林风眠校长虽也引用了西画教学的模式,但他更留意于西方近现代的绘画流派,他的教学除基础的造型训练外,多注重于画面形式和情感的表现,在他的影响下西子湖畔走出了赵无极、朱德群还有吴冠中。他们各具东方情调的形式语言拓展了新的绘画审美样式并借此成功地跨入了国际的艺术舞台,可以说这与林氏的教育思想不无关系。同时在此还值得一提的是潘天寿继林风眠之后执校长一职,无论在民族危亡的变革时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潘天寿一贯秉承中国画发展之文脉,坚信站在本民族绘画的基点上顺应时代之发展,坚持在中西文化保持各自特点的基础上要拉开距离,他尽一身之力传承中国画学正脉与道统,捍卫了中国画的尊严。两位校长的教学思想与方式虽不尽同,但都胸怀复兴民族绘画之大志,殊途同归。吾辈后学当慎思之。
美博会馆前不久诚邀我参加朱国荣先生策划的题为“致敬林风眠”画展,然我的画路与其主题似乎略有牵强,好在诚邀方和朱老师的宽容大度,我仅以此拙文一来向林先生表示敬意,二来亦算是弥补吾画之不足吧。邵仄炯【原标题:林风眠水墨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