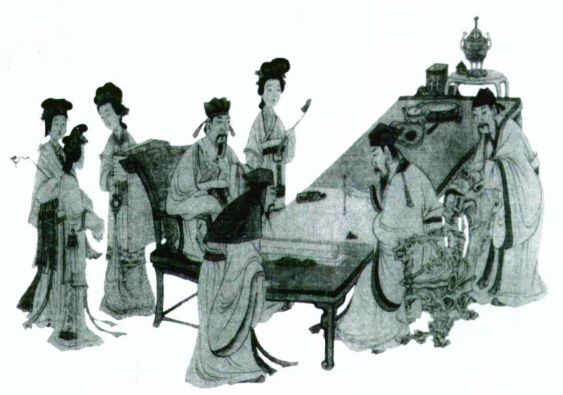-
没有记录!
堂号的来历
2014/7/9 15:58:24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赵姓的“半部堂”,出自北宋王朝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安天下”的典故。
周姓的“爱莲堂”,出自北宋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他在《爱莲说》中,曾赞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
谢姓的“东山堂”,出自东晋著名政治家谢安的典故。谢安,字安石,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淡薄名利,隐居会稽东山。在国家危难的关头辞别东山,出任宰相。指挥淝水之战大获全胜,继又北伐,收复青、兖、徐、豫等州;成为流芳千古的英雄人物。成语“东山再起”说的就是谢安。
刘姓的堂号“蒲编堂”,典出三国蜀汉皇帝刘备故事。东汉末年,刘备家居涿县,幼年丧父,贫苦无依,和母亲一起织席卖草鞋为生。起事后,常被政敌蔑称为“织席贩屦小儿”。刘备称帝后,常思其母编织蒲席之苦,茶饭无味。刘姓后人遂以“蒲编”为堂名,以告诫子孙勿忘祖先创业之艰辛,以简朴勤奋为本。
杨姓的“四知堂”,出自东汉杨震拒收贿赂的故事。东莱太守杨震路经昌邑,当晚昌邑县令王密求见。王密为讨好上司送来“十金”,并对杨震说:“三更半夜无人知晓。”杨震严肃地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人知道呢?”王密只得羞惭而退。杨震后来担任司徒、太尉等重要的职务。为了纪念杨震的一身正气、廉明清正,杨姓后人将“四知”作为家族的堂号,鞭策子孙效法祖先的清廉家风。
王姓的“三槐堂”,出自北宋王祜“植三槐,自知子必贵”的故事。王祜是开国名臣,曾任尚书、兵部侍郎等要职。他曾亲手在自家庭院里,种了三棵槐树,并预言说:“我的后代一定有担任‘三公’一类高官的。先用这三棵槐树当标志吧。”后来他的儿子王旦果然当上了宰相,天下人都称之为“三槐王氏”。“三槐堂”由此得名。
韩姓的“昼锦堂”,是北宋社稷重臣韩琦致仕归里,在相州故居修造厅堂之名。典出《史记"项羽本纪》,秦末项羽统兵破咸阳亡暴秦后,思归江东,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后以富贵还乡为“昼锦”。韩琦以“昼锦”为堂号,绝非小人得志后的矜夸炫耀;而另有深意——把“昼锦堂”诗刻于石上,以告戒自己和后人:夸耀名誉地位,是一种令人菲薄的陋行;而应当把功业荣华作为对自己的激励和儆戒。北宋文坛巨擘欧阳修在《相州昼锦堂记》一文中,对此论说甚详。
孙姓的“映雪堂”,出自西晋孙康映雪夜读的典故。孙康自幼笃志好学,家境贫寒,无钱买油点灯夜读,冬夜利用白雪反光刻苦研读。由于勤奋攻读,学富五车,官拜御史大夫。孙姓后人把“映雪”作为堂号,旨在激励子孙发奋读书,立志成材。
郑姓的“著经堂”,是赞颂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郑玄潜心著述,聚徒讲学,融会贯通,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从宋代开始,一些文人雅士喜欢把“堂号”署在诗文书画作品上。后来,干脆自己命名一个“堂名”,在文化交流时签署使用。实际上,这些文艺家已把家族的“堂号”逐步演化为个人的“斋名”。文人为书斋所取之名,又称为“室名”,例如:宋代文人蔡京的“六鹤堂”、陆游的“双清堂”,元代文人黄公望的“三教堂”,明代文人汤显祖的“玉茗堂”、吴文华的“济美堂”、谭元春的“岳归堂”,清代文人秦荣光的“养真堂”、陈廷庆的“谦受堂”等。
现代文学艺术家刘半农的“含晖堂”、丰子恺的“缘缘堂”、陈寅恪的“寒柳堂”、冯友兰的“三松堂”、张大千的“大风堂”、刘海粟的“艺海堂”、李可染的“耕牛堂”等都是著名的斋名。单字的斋名,在20世纪前期较为盛行,如王国维的“观堂”、鲁迅的“俟堂”、郭沫若的“鼎堂”、周作人的“知堂”、孙犁的“耕堂”、冯其庸的“宽堂”等,已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
近代许多政客、名人迁居天津,他们在天津购买私人住房时往往用“堂号”,却不用本人姓名。例如:
1905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以“树德堂袁”的名义买下河北区元纬路和地纬路之间20多亩土地,建起规模宏大的袁氏花园公馆。
1912年,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黎元洪在旧英租界盛茂路(今河北路),以“大德堂黎”的名义,购买土地,建造高级住宅。
1927年,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以“宝墨堂徐”的名义,购地15亩,建起8所住宅。
吉鸿昌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0年以“有余堂”的名义购置的。宋哲元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2年以“明德堂”的名义购置的。张自忠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6年以“安庆堂”的名义购置的。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铭在天津的住所,是1931年以“大福堂”的名义购置的。爱国工商业者周叔弢先生的寓所,是1935年以“诗礼堂”的名义购27亩建造的;爱国实业家毕鸣岐先生的寓所,是1944年以“永顺堂毕”的名义购买的。
政要名流购买私人住宅乐于用“堂号”之名签署登记,究其原因,一是为了显示家族的声望和地位;二是不必显示张扬自己的姓名。这种作法也体现出天津近代民俗的一种习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