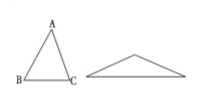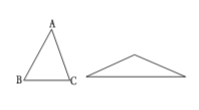-
没有记录!
《水浒传》里的地理学
2013/9/30 10:32:15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一
用常人眼光来看,《水浒传》中的地理都是有问题的,而从头到尾,错得毫无商量余地的彻底——和宋公明那种打打再商量招安的半推半就策略,风格截然不同。
史进离开华阴县的少华山,“取路投关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来”。(《水浒传》第二回)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半个月后,史进却来到渭州。要知道,渭州,就是今天的甘肃平凉,在延安西南,渭州到延安直线距离280公里(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39页)而出发地华阴在延安南略偏东,两地直线距离240公里,华阴与渭州直线距离330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55页)。三地关系,可以用下图示意。延安在顶点A,渭州在左点B,华阴在右点C。按照常理,史进应该采取CA线;但他实际上走了CBA的线;绕远得有点说不过去。就是说,渭州根本不在史进行程路线之内!
鲁智深离开五台山,投奔东京大相国寺,路过青州地面桃花山。(《水浒传》第四回)青州属京东路(《宋史》卷八十五),离渤海湾只有一百多里地。五台山则在河东路代州雁门县(《宋史》卷八十六)。青州在五台山东南,两地直线距离约500公里;东京在五台山南略偏东520公里;东京距离青州420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44页)。这又是一个三角关系。我们用A指五台山,B指东京,C指青州。鲁智深去东京,当取AB路线,他却是ACB路线。现实中是根本不行的。
庆历二年(1042年),建大名府为北京(《宋史》卷八十五),就是说,《水浒传》中的北京,是现在的河北大名。杨志押送的蔡太师的生辰纲由此出发,目的地是东京。北京大名府去东京直线距离204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44页)。杨志只要朝南偏西走就行了,但他的路线大大地往东偏了,一直偏到济州的黄泥岗!(《水浒传》第十五回)北京去济州,138公里,东京去济州180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44页)。仍用三角形来说明:A是北京,B是东京,C是济州。杨志本当采取AB线,但实采取ACB线。
江州蔡九知府派神行太保戴宗到东京给他爹蔡京送生日礼物和家书,叮嘱戴宗“切不可沿途耽阁(搁),有误事情”!戴宗因为还想到东京为押在大牢里的宋江走走门路,所以也是力求尽快赶路(《水浒传》第三十八回)。但他竟然来到梁山泊边上的朱贵酒店里打尖!要知道梁山泊并不在江州去东京的线路上。江州去梁山泊直线距离660公里,江州去东京600公里;东京在江州的北偏西;梁山泊在江州北;而且梁山泊又在东京的东北,两地120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45-46页)。三地又生出三角关系,而且是钝角三角形。假设:A东京,B江州,C梁山泊。戴宗当走BA线,实际上却是BCA线!
无为军,是在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设立的,“以庐州巢县无为镇建为军,以巢、庐江二县来属”。(《宋史》卷八十八)无为军靠近长江,在江州的下游,与江州的直线距离是252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50页)。《水浒传》却告诉我们,“这江州对岸,另有个城子,唤做无为军”,而且无为军的闲通判黄文炳能一叶扁舟,三天两头地从无为军过江来频繁地探望江州蔡九知府(《水浒传》第三十八回)。也就是说,江州与无为军之间这二三百公里的长江,在《水浒传》中给抹得干干净净,截断,扔掉了!
蓟州,就是现在的河北蓟县一代。它在宋代,先是辽国属地,后是金国属地,根本不在宋的版图之内。直到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蓟州来归”(《宋史》卷二十二)。而《水浒传》明白地说,宣和二年四月一日,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在这以前,不但公孙胜老早在蓟州居住,而且杨雄也在蓟州城里做“两院押狱”。似乎蓟州本就是大宋的一角河山,而且中央政府进行着有条有理的管治,毫无问题。这就罢了。奇怪的是,戴宗从梁山泊出发往蓟州,他绕道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要从沂水县边上过(《水浒传》第四十三回)!沂水是沂州的辖县(《宋史》卷八十五),沂州在梁山泊的东南198公里;蓟州在梁山泊北部偏东,距离510公里;而蓟州在沂州的北部偏西,距离576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44页)。戴宗又制造出一个钝角三角形。假设A是梁山泊,B是济州(沂水),C是蓟州。戴宗当取AC线,但他实际上行的是ABC线。
以上是梁山泊英雄招安前的一些地理问题。此后征辽、征王庆、平方腊,我们不暇一一列举。实际上,早有人注意到水浒传对梁山附近地理描述是不正确的,归结为“为情节需要而随便改动”,或者“传抄错误”。(刘华亭《水浒传中梁山附近的地理描述》,载1998年第5期《济宁师专学报》)虽言之有理,但过于简略。
二
我们知道梁山泊英雄奔赴目的地时,和常人一样遵循就近原则,尽量走两地间的直线,避免曲折绕远。也就是说,《水浒传》暗示,他们并没有绕远,现实中看去之字路线,在小说中是不存在的!渭州,就在从华阴到延安之间的路上,是个必经的中间站。无为军就在江州的对岸,隔江相望,并没有二三百里的滚滚长江。
如何解释它与现实的牵连与纠结?对于诗文中的风物与现实中的风物不相吻合这一现象,钱锺书解释说:“诗文风景物色,有得之当时目验者,有出于一时兴到者。出于兴到,故属凭空向壁,未宜缘木求鱼;得之目验,或因世变事迁,亦不可守株待兔。”(钱锺书著《管锥编》,三联书店,2007,第154页)在诗史、文史的传统下,诗文风物尚且与现实龃龉不合。何况小说,何况小说中的地理怎能与现实贴切?这也可以解释《水浒传》中的地理学问题。但仍然有点笼统,好像袁中郎所谓“一个八寸三分的帽子人人戴得”(袁宏道《与张幼宇书》)!
宋元时候,演义小说刚刚兴起,作为一种文体,它没有明确的规定性,可以天马行空,自由发挥作者才情。因为先出现的是《三国演义》,它是七分真实三分虚。它影响极大,效果强烈,所以,不知不觉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认为历史演义,都应该注重历史真实;人们对后出现的《水浒传》自然也这样要求。比如金圣叹就拼命把它和《左传》《史记》拉扯到一起,大谈历史的“精严”(金圣叹《批评水浒传序三》)。其实,《水浒传》已经走上一条与《三国演义》截然不同的路子,《水浒传》只剩下一个框架是有点历史根据的,可以说十之八九都是虚构。
其实,不光我们的历史演义小说受到不合历史真实这样的非分责难,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司各特的历史小说,都曾受到同样的非议。历史小说,为了和现实划清界限,不少小说家,为他的小说人物创造出完全的新世界作为活动空间,比如英国作家约翰·罗纳德·鲁埃尔·托尔金《指环王》三部曲(The Lord of the Rings),美国作家乔治·R.R.马丁《冰与火之歌》四部曲(A Song of Ice and Fire)。
我们的《水浒传》作者由于历史的局限和传承,当然无法使小说和历史现实完全隔绝,也没有将其中的地理和现实划出明确的界限;有误导看官的嫌疑。但在小说有着明确规定性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再将之混淆在一起,纠缠不清。所以,不能用现实的尺度去衡量《水浒传》中的地理学。或者说,《水浒传》中的地理学是真的(true),但不是实的(not real),它和现实没有对应关系,只在《水浒传》设定的领域内具有有效性与正确性。一出界,它就失效了。如果一定要拿它做别的用途,那也是各人的自由,《水浒传》的作者对此并不负有什么责任。就好比阿司匹林本来是退烧的处分药,后来却作为非处分药,拿去降血压。但拿《水浒传》中的地理学去到现实中用,是否会产生阿司匹林那么幸运的效果,可就难说了。还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吧!周岩壁(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原标题:《水浒传》里的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