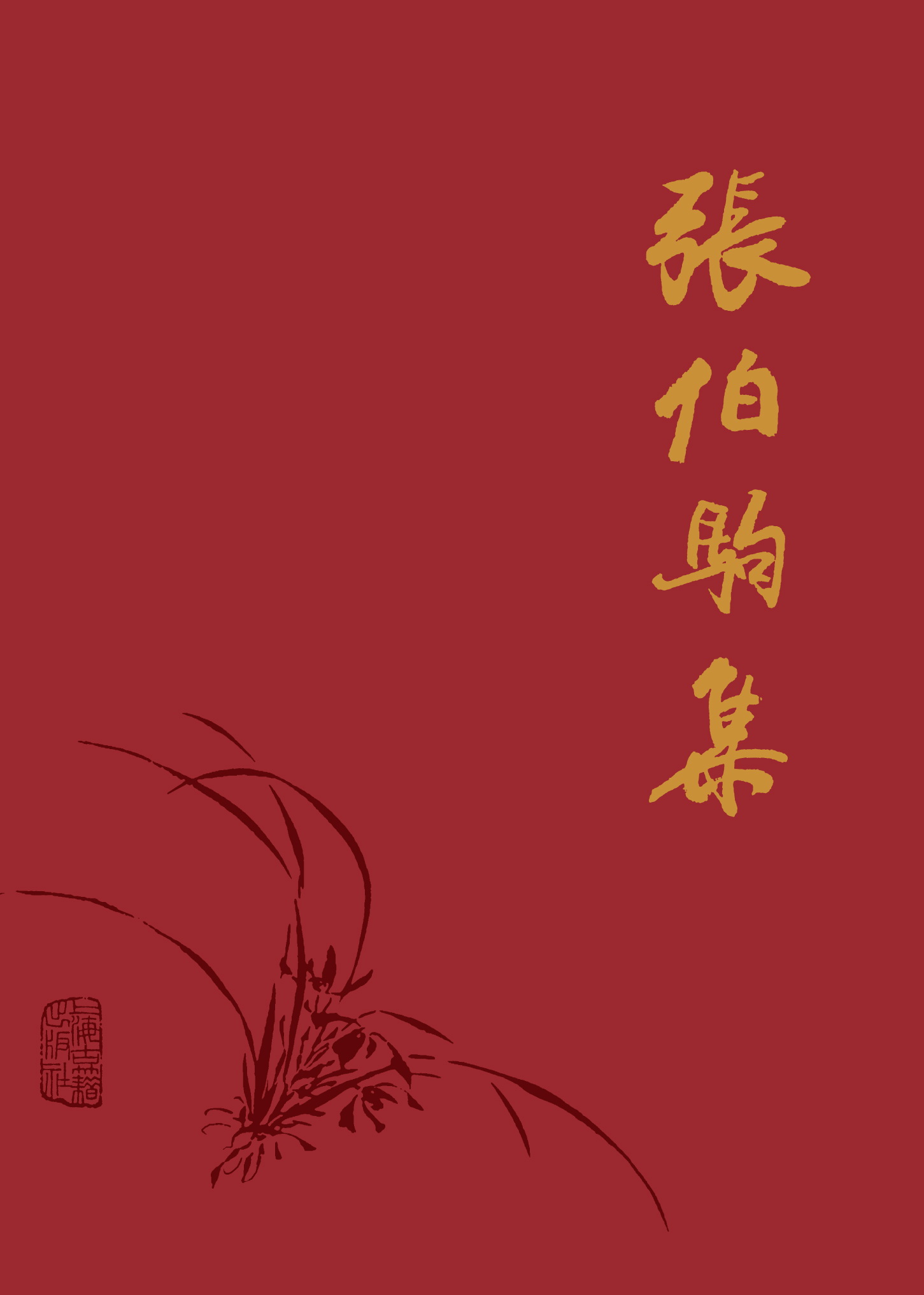-
没有记录!
张伯驹和京剧——读《张伯驹集》随笔
2014/12/24 10:44:48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张伯驹对于中国戏曲艺术具有广博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以此做出了很多独到的评论。这些评论,也许不够全面,那是因为他过分局限于“神韵”这唯一的标准,而对其他美感有所忽视,这才会有对言菊朋和马连良的过分贬损。但从深刻性来看,确实够得上“第一义谛”。
张伯驹先生在中国戏曲界的名声颇盛,趣闻尤其多。只是口耳相传一久,就不免越传越走样,其形象也就不真实了。这不真实的形象,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张伯驹戏曲艺术研究价值的认知。因此,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的《张伯驹集》,甚为兴奋。毕竟,张伯驹亲手写下的东西,对于我们认识他的戏曲研究至关重要。
张伯驹的著作出版已久,重印的不多,所以搜求不易。这次出版的《张伯驹集》,将他的著作一网打尽,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中和戏曲尤其是京剧相关的资料主要是《红氍纪梦诗注》和《乱弹音韵辑要》。(《乱弹音韵辑要》可谓京剧音韵学的扛鼎之作,但研究太专业,这里就不评述了。)另外,《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和《春游琐谈》里也有一些,只是前者和《红氍纪梦诗注》重复了不少。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容易地看到,一些传闻实在不可靠。
比如说,大家一般都认为,张伯驹在京剧上的独到之处,是靠了丰厚的束脩和诚恳的态度,从余叔岩那里学到不少“掏心窝子”的东西,因此,他是个“纯余派”。捧之者如此说,贬之者也如此说。可是不论捧之贬之,都有这个言外之意:张伯驹不知道也就不懂别的流派,只懂余派。如果看看他自己的文字,就知道这是个误会。
张伯驹对于京剧的兴趣,是从幼年培养起来的,并不是因为结识了余叔岩。他五岁被过继给伯父张镇芳(生父叫张锦芳),七岁跟随张镇芳来到天津,从此开始了他看戏的生涯。天津作为京剧演出的一个重要码头,名角演出极多。根据《红氍纪梦诗注》的记述,他看过的老生名角就有谭派创始人谭鑫培、孙派创始人孙菊仙、刘派创始人刘鸿声、许(荫棠)派传人白文奎,还有“小小余三胜”时代的余叔岩。另外,武生杨小楼、李吉瑞,武丑张黑,武旦九阵风,刚出科的青衣尚小云等,也是他看过的。甚至其他地方戏他也看。不过那时候他的欣赏水准还不够,所以两次看谭鑫培,都不知欣赏。“余十一岁时,……偶过文明茶园,见门口黄纸大书‘谭’字,时昼场已将终,乃买票入园,正值谭鑫培演《南阳关》,朱粲方上场,余甚欣赏其脸谱扮相,而竟不知谁是谭鑫培也。”(《诗注》一三)“先君寿日……谭扮戏时,余立其旁,谭著破皇靠,棉裤彩裤罩其外,以胭脂膏于左右颊涂抹两三下,不数分钟即扮竣登场,座客为之一振,惜余此时尚不知戏也。”(《诗注》一九)也就不能分辨演员的高下,他说:“当时谭、刘、孙齐名,但余在童时尚不懂戏,孰为高下,则不知也。”(《诗注》二七)不过他七岁时却学会了孙菊仙的唱法。“余七岁时,曾在下天仙观其演《硃砂痣》,当时即能学唱‘借灯光’一段,至今其唱法尚能记忆。”(《诗注》二)相信幼时的张伯驹,对于京剧肯定是很熟悉的。甚至还会唱几句山西梆子。“元元红山西梆子老生唱法,人谓其韵味醇厚,如杏花村之酒。有人谓其《辕门斩子》一剧,尤胜于谭鑫培。余曾观其演《辕门斩子》,其神情作风,必极精彩。惜在八九岁时,不能领会。惟尚记对八贤王一段唱辞。……童时余还能学唱。”(《诗注》一〇)
幼年的熏陶使得张伯驹逐渐对于中国戏曲艺术有了深入的认识,也形成了极高的欣赏品味。他认识到,中国的戏曲艺术和其他传统艺术具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它们具有相同的衡量标准。标准中最高的,他以“神韵”来概括。他说:“王渔洋诗主神韵,有论诗品诗,如其《过露筋祠》诗……即富于神韵者。词以到禅境为最佳,如南唐后主词‘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北宋晏小山词‘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皆臻禅境,亦即神韵。余自七岁观剧,而认为堪当神韵二字者只有五人,乃昆乱钱金福、杨小楼、余叔岩、程继仙,曲艺刘宝全也。汪桂芬余未赶上,谭鑫培、孙菊仙余曾赶上,但在童时,尚不懂戏也。”(《诗注》一〇七)这是他自己的心得,余叔岩未必能够概括出来。可见,张伯驹选择余派,不是因为偶然结识余叔岩的机会,而是基于多年的鉴赏实践后高度的理论概括。说他只懂余派,显然是“想当然耳”的说法。再说,以他当时对戏曲的痴迷和经济能力,怎么会不去看看别人的演出呢?而且,张伯驹也学过余派之外的戏,如跟钱金福“学《五雷阵》《九龙山》两出,一饰孙膑老生戏,一饰杨再兴小生戏”。(《春游琐谈·赠钱金福金缕曲词》)当然还不止此。因此,说张伯驹不懂余派之外的戏,纯属误会。
当然,有关张伯驹的传闻走样失真,也不是没有他自身的原因。出身贵公子,不免带上些习气。习惯了受人逢迎的张伯驹,往往天真地把别人的客套当做了现实,有些话看来实在太像自我标榜了。他说:“夏日院内置藤椅竹床,客坐于外,余与叔岩在室内吊嗓,彼唱《桑园寄子》,余则唱《马鞍山》;彼唱《马鞍山》,余则唱《桑园寄子》。外面客不能分为谁唱,必至室内问询,始知也。”(《诗注》一四二)“与尚小云演《打渔杀家》,小云大为卖力,内行谓之曰‘啃’,是日对啃,演来极为精彩,台下甚为满意。后有人云‘尚小云未啃倒张某人’,一时传为话柄。”(《诗注》一六四)张伯驹的说戏录音还有流传,带有较重的河南口音,说他的唱和余叔岩不能分辨,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毕竟是票友,缺乏专业演员高强度的幼工、演出锻炼,要和名列四大名旦的尚小云争长,恐怕也只能说是自不量力。
一旦别人把他这样的习气看作自我标榜,就会认为他的戏曲艺术评论也出于标榜。比如,不少人会认为,张伯驹只捧和余叔岩关系好的演员,反之,就加以贬损。其实,这也是个误解。基本上说,张伯驹的评论还是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理论的。他既以“神韵”作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最高标准,对于其他演员的衡量,也都是根据这个标准的。“神韵”要求摆落人工痕迹和感官愉悦,就和雕琢、甜熟格格不入。所以,张伯驹最倾服余叔岩,却很不喜欢言菊朋和马连良。他说言菊朋:“菊朋后下海演老生,宗谭鑫培,自命为谭派传人。梨园内行嘲其为‘言五子’……按言亦知音韵,如阴平高念,阳平低念,上声滑念,去声远念,入声短念之类;但不知变化运用,每韵尚有三级之妙;又以嗓左,遂至学谭反而映山隔岭,奇腔怪调,无一是处。”(《诗注》七八)按说,言菊朋和余叔岩同宗谭鑫培,张伯驹不该对言菊朋评论如此苛刻,所以有人以为是言菊朋和余叔岩存在竞争关系,张伯驹刻意贬低言。但实际上,言菊朋学老谭,几于亦步亦趋,技巧的运用不够空灵,加上为嗓音所限,晚年唱腔更是走向险怪。这就不免于雕琢,和张伯驹的“神韵”标准相去较远。他说马连良:“马连良初师贾洪林,后亦不似,《借东风》为其拿手戏。但武侯知天文学,计时应有台风,因用火攻破曹军,非能借东风也。连良演此戏,竟使武侯如一妖道,乃腹无文学之故。”(《诗注》八一)这都近于吹毛求疵了,但仍然是因为马连良“腹无文学”的原因。即马连良的唱腔过于甜熟,近乎“元轻白俗”,显得缺少深湛的修养,和“神韵”相悖。可以说,张伯驹的评论还是从他自己的艺术理论出发的,和党同伐异没有关系。
对于这一点,可以举出一个反例。其实,余叔岩还有一个更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已经被人遗忘的王凤卿。余叔岩二次出山搭梅兰芳的“喜群社”时,头牌老生就是王凤卿。余叔岩一直被王凤卿压制,演出的戏码也要经常回避王凤卿的。由于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演出时,得到王凤卿的极力帮助,加之王凤卿确有实学,余叔岩无法动摇他的地位,最终自行组班。如果张伯驹真是党同伐异,对王凤卿也不应该有较高的评价,可是恰恰相反。他说:“王凤卿唱法用脑后音,为汪派传人。《过昭关》《浣纱记》《鱼肠剑》《取成都》《战长沙》皆其拿手戏。饰《战长沙》关羽,以胭脂揉脸,不打油红脸,乃取法程大老板。凤卿好书法,常临刘石庵、翁同龢书。余曾赠以刘石庵书册,彼甚宝之。”(《诗注》五九)没有任何贬损。究其原因,还是王凤卿的汪派古朴唱法和“神韵”是不大冲突的。
细读《张伯驹集》,不难看到:张伯驹对于中国戏曲艺术具有广博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以此做出了很多独到的评论。这些评论,也许不够全面,那是因为他过分局限于“神韵”这唯一的标准,而对其他美感有所忽视,这才会有对言菊朋和马连良的过分贬损。但从深刻性来看,确实够得上“第一义谛”。所以,《红氍纪梦诗注》历述京昆名角,简直可以作为一部民国京剧小史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