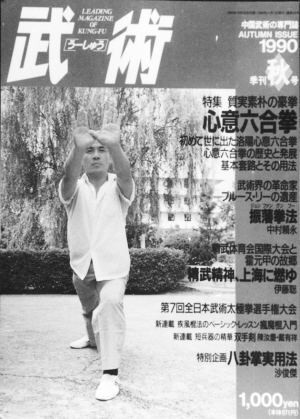- 1、汴绣工艺特征及制作工艺
- 2、中原一绝 珍品汴绣
- 3、“汴绣”获注 开封实现地理标志证明商
- 4、走进开封体验千年汴绣精髓
- 5、寻访马坡八卦掌传人
- 6、汝州三宝之“汝帖”
- 7、剪纸的文化背景
- 8、三官庙挠阁: 独领风骚三百年
-
没有记录!
宝丰 魔力(上)
2013/9/10 17:54:50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核心提示】
全国玩魔术的人,有一半来自河南宝丰。这不是夸张。
今年8月22日,中国杂技家协会正式授予宝丰县赵庄乡“魔术之乡”的称号。这个地方的魔术史已有千年之久,宛如一眼泉水,汇成滚滚洪流。周营村的魔术在最近20年内蔓延到所在的赵庄乡,又蔓延到所在的宝丰县。魔术,每年为宝丰县带来的收入超过3亿元,创造的百万富翁超过1000个。
10月10日,中国宝丰第三届魔术文化节在这里开幕。10月20日,省委书记徐光春在持续关注宝丰魔术几年后,第一次亲赴此地调研。
《非常档案》特推出“宝丰魔力”系列报道。对“魔术之乡”光环背后的宝丰文化进行一次标本解读。
“徐书记,你拿回去多练练,就也会玩魔术了……”
10月20日下午,宝丰县周营村,村民靳全亮当着省委书记徐光春的面表演了一个魔术。
“徐书记,这是我专门从西藏带回来的银杯,你看,杯子里是空的。”银杯口朝下,一点酒也倒不出来。但是,随后他双手一晃,银杯子里竟然装满了红酒。徐光春书记接过来一尝:“哟,还是真酒!”随后他打趣说:“要是都像你这么变出酒,酒厂都要关门喽。”那天,给徐光春书记一行表演魔术的村民很多,其中既包括9 岁的女娃张小伟,也包括45岁的宝丰县民间演出协会会长刘顺。刘顺还给徐光春书记讲了小魔术《圆珠笔穿纸》的诀窍,并把几组道具送给徐光春书记,说:“徐书记,你拿回去多练练,就也会玩魔术了……”
徐光春书记笑着应道:“好,好……”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顺蹲在地上,顺手捡了块小石子,说:“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给你玩两招。”他把石子放在左手,说:“看,石子在我左手里。”说完,握紧左手。然后,他的右手轻轻划过左拳。待左拳再伸开时,小石子已不翼而飞,而右手也空无一物。
“去哪了?在你口袋里。”刘顺自问自答。说着,刘顺往前迈了一步,飞快地伸手从记者的上衣口袋里“摸”出刚才那颗小石子,呵呵一笑。
刘顺露的这几手,周营村80%的人都会。周营村70多岁的靳老汉说:“我不喜欢玩魔术,但他们玩的魔术,我都知道怎么玩,村里人都知道。”
魔术绵延不绝背后的贫穷抗争
拿小石子玩小魔术时,刘顺蹲在周营村入口处,旁边,他投资的宝丰四通瞬发魔幻培训基地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
这个工程投资80多万元,占地2亩。“楼上是表演厅,楼下卖魔术道具,那边规划的是餐厅、宾馆。”刘顺指点着说。是时,刘顺穿着白衫衣,套着黑夹克,衫衣口袋里一沓百元大钞遮着一盒5块钱的红旗渠香烟。他开玩笑地拍拍口袋说:“咱就是有钱。”
贫穷曾经给刘顺带来无尽的悲伤,那样的日子不堪回首但无法忘却。家中兄弟姐妹8人,刘顺排行老大。上世纪70年代,因为家里吃饭的人多,生活异常困难,一家十口人没一间房,经常在生产队的牲口棚里住。
16岁那年,刘顺想去洛阳谋生。他身上没有一分钱,只好扒煤车,谁知道被拉到西安。在沿街乞讨的时候,他遇到了改变其人生的江湖艺人王志富。
刘顺知道村里有人玩魔术,却没想到,王师傅在街头玩魔术一天竟能赚20多元。刘顺跪求王师傅收他为徒。半年后,他学了20多种魔术,开始单独练摊儿。
几年后,母亲得了癌症,刘顺不得不回到家乡,在宝丰附近的鲁山县、郏县等地表演魔术挣钱。
当地的不少农民魔术师都有类似的苦难经历,因为改革开放前的赵庄乡“十户九缺粮,家家住草房”。
也许赵庄魔术能从唐宋兴起、在明清繁衍、传至今天,与贫穷抗争才是主要原因。
“大卫·科波菲尔没什么了不起”
20世纪80年代,“变戏法”并没有让刘顺暴富。他相亲时穿的是舅舅的衣服,“老婆开始也看不上我这个穷孩子,现在看来她嫁给我是很有眼光的”。刘顺自豪地宣称,他亲眼见证了赵庄魔术的变迁。
1989年,刘顺组织了一个魔术团,带着刚过门的妻子,开始到湖南、安徽、山东等地“卖艺”。
他只身一人闯青岛时,在公园里用布围个场地售票演出。后来,出去表演就用简易的大篷,有个话筒就感觉“美得很”。再后来,大篷越来越豪华,音响越用越高档,演出团的人员也从十几人发展到上百人。而现在,许多演出团开始与一些大城市的演艺厅签约,串场表演,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因此,魔术表演的道具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什么人头移位、什么怪胎展览……运用舞台背景、运用声光电等技术的魔术也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赵庄魔术演出团的节目也越来越多,包括杂技、气功、舞蹈、演唱。“这两年魔术吃香,得感谢美国的魔术大师大卫·科波菲尔。”刘顺说。
2004年,大卫巡演到北京,让中国人更深刻地认识了魔术的奥妙,也把中国魔术带入新的发展时期。
尽管感谢大卫,尽管吸收了大卫的不少表演技巧,但是,包括刘顺在内的不少赵庄乡魔术师都认为,大卫没有什么了不起,在他的魔术中道具是主角,无论谁来替大卫,都能让自由女神消失。“魔术的功力如何还是要看‘手法’”。手快、眼明、活干净,赵庄魔术的精髓仍在“手”上。
“买辆奥迪,逢年过节回家了,开着玩玩”
周营村的刘顺们挥舞魔棒,把生活“变”得很富足,附近的大黄、小黄、白店、大韩庄、木中营等村庄也跟着玩起了魔术。上世纪90年代,赵庄魔术很快辐射到商酒务、肖旗、石桥等相邻乡镇,影响了整个宝丰。
60多岁的靳拴(化名)是记者偶然碰到的一个大黄村村民。那天黄昏,他骑着一辆28式自行车正往家里赶,家里只有老伴在等他。
他的4个儿子都出去玩魔术了,“每人带了一个演出团”。靳拴住的是两层楼,院里种着花,还放着一辆被雨布遮得严严实实的轿车。轿车崭新,是奥迪A6,1.8升排量。靳拴轻描淡写地说:“我不开,这是小儿子买的。逢年过节回家了,开着玩玩。”
小儿子除了这辆轿车,还在宝丰买了一套别墅,在平顶山市区买了一套近二百平方米的房子。
富起来的不是一两个人,周营村有魔术演出团112个,从业人员880人,占全村总人口的1/2,年收入2000万元,周营村平均每两人拥有一部手机,有豪华轿车15辆、面包车23辆、大客车63辆、摩托车322辆,人均年收入1.2万元。
2005年春节前一个月,每天赵庄邮政所收到的汇款达10多万元,最高一天汇款达28万元。
赵庄乡有22个行政村、3.6万人,有魔术等各类表演团体632个,从事演出的民间演职人员达1.2万人,年创收超亿元。
而整个宝丰魔术表演收入去年达到3.3亿元。一个经常引用的说法是:“全国有2000多家、宝丰有1400多家民间演出团体,从业人数5.5万人,团体数量和从业人数均占全国的半壁江山。”
看得见的光鲜看不见的酸楚
刘顺的妻子陈秀云17岁时就随团出去表演。嫁给刘顺后,又跟随刘顺去天南海北流浪。
现在,刘顺设计魔术道具,陈秀云带着女儿设计魔术服装,都不再出去流浪,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从台前转向幕后”。但是,吃魔术这碗饭注定了“走四方是一种生活常态”。
周营村一个魔术团的团长李耀光说,带团出去,钱是挣得不少,治安也可以,可是“那种一直在路上的感觉不好”。
李耀光说:“在一个地方最多呆7天,一般都是两三天就要换地方,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从一个场子到另外一个场子,这种感觉,让人很累。”
大黄村王老太的几个孩子都带团演出,只剩下她和老伴。她说:“天天操心他们。一天接不到电话就睡不安稳。”父母们看到的不是他们挣了多少钱,而是他们吃的苦受的罪。
陈秀云说:“我们得到了不少,也失去很多,特别是教育孩子方面。”
她的儿子就是在湖南省邵东县演出时生的。因为经常出去演出,一年请一个家庭教师带儿子,儿子给别人说“一年换一个家长”。
因为常年在外演出,陈秀云和刘顺觉得欠孩子们不少,所以,“为孩子成长,花多少都在所不惜”。他们的儿女上初中时,被送入平顶山市的贵族学校,两个人一学期的学费是1.8万元。但初中毕业后,俩孩子说啥也不愿意上学了。
这对陈秀云来说是个遗憾。陈秀云说:“知识就是力量,还是上大学好,有地位。有地位就有一切。”
人们知道的是,农民魔术师奔波于小桥流水的江南、冰天雪地的东北,从外地赚回一沓沓的钞票,盖新楼买房子坐小轿车。
人们不知道的是,他们根本无法观赏美丽的景致,无法留恋城市的繁华。殷实生活的背后是吉普赛人一样的流浪,每个人都有流浪的艰辛和心灵无所依附的落寞。
还有一点不愿意告诉别人的是,虽然他们演出的设备和环境越来越好,但是市场和社会的评价始终让他们觉得距离艺术两个字太遥远,“不过,一切会越来越好,我们将来会和大卫一样风光。”30岁的李耀光说。【原标题:记者 路治欧 史玉琴\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