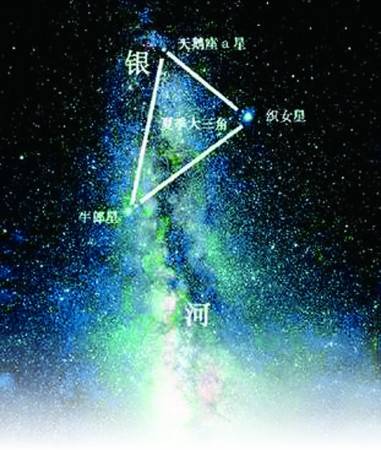精彩推荐
热点关注
- 1、钧瓷发展经历的几个重要阶段
- 2、比赛竞技显风采,象棋文化得发扬
- 3、钧窑瓷器的价值
- 4、商丘古城里的“闹龙街”
- 5、相思树
- 6、钧瓷新探寻
- 7、无声的钧瓷
- 8、“白蛇传说”起源于鹤壁淇水黑山
专题推荐
-
没有记录!
热点排行
- 1、钧瓷发展经历的几个重要阶段
- 2、比赛竞技显风采,象棋文化得发扬
- 3、钧窑瓷器的价值
- 4、商丘古城里的“闹龙街”
- 5、相思树
- 6、钧瓷新探寻
- 7、无声的钧瓷
- 8、“白蛇传说”起源于鹤壁淇水黑山
中国佛教与白马寺清凉台
2012/4/18 9:28:46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引言: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印度传教者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中国,并住在当时明帝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为他们建起的精舍,即洛阳白马寺里。此后,佛教便在中国广泛流传,此间在思想上也曾经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论,但就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调融,终于汇入中国文化的巨流,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并对我国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佛教 清凉台 摄摩腾竺法兰《三教调和论》
第一本汉文佛经在清凉台上译出
《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故事,妇孺老幼皆知,唐僧师徒历经八十一难,终于取得真经,功德圆满,这显示了修佛的艰难。
实际上,取回真经只是佛学路上的第一步,要想有所成就,必须读懂真经。
佛教传自印度,所以最早的佛教典籍都是梵文版的。要让中国人看懂这些典籍,翻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要让人接受,得先让人懂啊!所以在佛教传入我国的初期,译经是僧人们的重要活动。
在白马寺清凉台,这是一个特别的所在,这里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出发点。
清凉台是个砖砌的高台。这个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地方,有着很多的内涵,它把译经这段重要的历史内容浓缩在了这里。
相传,清凉台原是汉明帝刘庄小时候避暑、读书的地方。后来两位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来到洛阳,被安排在此居住并译经传教。第一本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就是在清凉台上译出的。两位印度僧人在清凉台上的译经工作,奠定了白马寺作为中国第一译经道场的地位。
印度高僧殿位于清凉台上毗卢阁前东西两侧。东侧为摄摩腾殿,西侧为竺法兰殿。分供摄摩腾、竺法兰之泥塑像。这两位大师,永远留在了中国佛学史上。
一千九百年后的今天,在白马寺山门之内,东西两厢围墙之下,苍翠茂密的柏树林中各有一座用弧形青石围砌起来的圆冢。东边圆冢的墓碑上刻着“汉启道圆通摩腾大师墓”,西边圆冢的墓碑上刻着“汉开教总持竺法大师墓”。“启道”、“开教”,这就是后人对两位高僧的评价。
佛教多个宗派在清凉台上相会
东汉以后,清凉台成为白马寺的藏经之所。在白马寺“六景”中,清凉台高居首位。清凉台的中心是毗卢阁。在毗卢阁周围,环绕着配殿、僧房和廊庑等。清凉台在白马寺整个古建筑群中自成格局,被人誉为“空中庭院”。
毗卢阁是白马寺的最后一重大殿,为明代重修。毗卢阁内佛坛上中间主尊为摩诃毗卢遮那佛,简称毗卢佛,意为“大日佛”,象征着光明普照,佛法广大无边。毗卢佛是佛教中一个重要教派——密宗(也叫真言宗)所尊奉的最高的神。
毗卢佛的左侧为文殊菩萨,右侧为普贤菩萨。这一佛二菩萨,合称“华严三圣”,均为清代泥塑像。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后,逐渐走向兴盛。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佛教宗派。这些宗派之间互相联系,互为影响。这些宗派中比较重要的有禅宗、净土宗、密宗、律宗等。作为“释源”和“祖庭”的白马寺,对于佛教的这种历史现象有明显的反映。
宋元之后,白马寺虽为禅宗寺院,但寺内的接引殿及阿弥陀佛主要是净土宗的内容,而毗卢阁及毗卢佛,则又主要是密宗的内容。
清凉台的东西两侧,分别新建藏经阁、法宝阁各一座,其中供奉着泰国佛教界赠送给白马寺的中华古佛和印度前总理拉奥赠送的释迦牟尼铜像。
中国佛教文化从清凉台出发
摄摩腾、竺法兰之后,安世高在汉桓帝时来到洛阳白马寺。安世高在白马寺共译出佛经95部150卷。据《开元释教录》载:从东汉至西晋,先后出现译师34人,译出经书700多部1400多卷。这些成就基本上都是在洛阳白马寺取得的。从东汉到清代,有许多人先后加入到翻译佛教典籍的队伍中。汉译佛教典籍的数量之大,品类之多,实为世所罕见。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开始于洛阳白马寺。
三国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佛教界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这一年,印度和尚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一卷。根据这部佛经的内容,昙柯迦罗主张僧众应遵佛制,守戒法,并请梵僧立羯磨法在白马寺建坛传戒,开中国传戒先河。其后不久,安息和尚昙谛来到洛阳,译出《昙无德羯磨》,并根据戒律的规定举行传戒仪式。
近年来,这样的传戒大会,在白马寺依然举行。1989年、1990年、1992年、1993年和1996年,白马寺先后五次传授三坛千佛大戒。1993年的传戒大会上,受戒者达到了创纪录的1800余人。据统计,这些受戒者来自全国各地和日本、美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
中国人出家,有人说始于东汉末的严佛调(安世高弟子),但也有人说,严只是居士,并未出家。如果后一说是准确的话,那么最早出家的名人,应该是三国魏时的朱士行。朱不只是最早出家的,他还曾西行求法。朱士行研究般若,但中土经典有限,于是在魏末(公元260年),他前往西域寻求佛法。在西域,他得到《大品般若》数十万言,于西晋初年命弟子送回洛阳,他后来一直没有回来。有了戒律的规定,出家人开始逐渐增多,据说到西晋时已有僧尼三四千人,当时仅洛阳、长安就有僧寺近200座。这个时期也有不少人西行求法,著名的有宋云和惠生。他们到达西域许多地方,取来不少经论,并著书记录西行的经过(《洛阳伽蓝记》卷五专记此事)。
后来,经过中国化的佛教由我国东传到高丽、百济、新罗和日本。这些国家都有不少僧人来长安学习佛法。
翻看历史的时候,抑或是翻看野史演义的时候,我们都不能不特别青睐唐代。唐朝时经济文化都很发达,佛教也处于鼎盛时期。唐代最著名的佛教人物莫过于玄奘。历史上的玄奘,绝对不是电影电视里那般懦弱和窝囊的样子,他是个对佛教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玄奘于唐太宗贞观三年出发,经西域到印度,往返17年,取回佛舍利150粒、经论657部、金檀佛像7躯。无论是在取经、译经方面,还是在佛学成就方面,玄奘都高居同时代出家人的首位。实际上,玄奘只是唐朝众多西行求法者的一个。据《大唐求法高僧传》记载,仅唐朝初年,西行求法的就有60人。
以白马寺《四十二章经》为开端、以唐朝洛阳为代表的佛教译经,成为博大精深的唐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唐朝文化的传播,这些汉译佛教经典远及日本、朝鲜等地,为佛教文化在东亚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交融
在中国文化史上,佛教是第一次大规模移植的外来文化。佛教文化传统包括信仰、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活等不同层次的理念与实际行为。任何文化都有其整体性与个别性,因此,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接触之后,必然会经过冲突与调和的过程,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都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佛教与中国文化之间,从冲突到调和的发展历程,就是文化史上一段重要的历史经验。
一、社会经济方面
佛教来华之后,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传布普及,寺庙林立。但在这段时期,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也开始表面化。而以社会方面的冲突较为显著。
佛教主张剃度出家,与中国的家族伦理颇有扞格之处。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攻击佛法的人士就站在传统孝道的立场,认为出家遗弃父母,断发毁伤身体,有违孝道的原则。他们也指出,佛法不事生产,使国空民穷。佛门中人及支持佛法的人士则以佛经作为依据,引用父母恩重难报经等佛经,说明佛教也注重孝道。例如:刘勰就指出,佛门人士与中土人士的行为虽有不同,但孝道之目的则属一致。他们更据史实说明佛法流行无妨于国家经济。魏晋南北朝时代这一类的辩论,对于增益双方人士的相互了解颇有帮助。
二、政治方面
君臣之义是传统中国政治伦理的重要部分,佛教沙门不礼拜君王,争论遂不可避免。晋成帝幼年即位,辅政的庚冰要求沙门礼拜君王,引起争议。安帝时,论难更趋激烈。
佛门人士则指出,沙门出家,不必拘泥于世间礼法;沙门不敬王者,原系印度佛教规仪,在中国行此法并非抵抗王权;而且,沙门不敬王者亦早已约定俗成,不必更改。慧远所撰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更为佛教人士的看法提供了理论的基础。这项争论一直绵延到明代,而有父母与出家儿子互拜的调和论出现、加速了佛教的中国化。
三、思想方面
佛教与中国方文化在思想层面上的激荡,最著名的是南北朝时代范缜所提出的神灭论。
范缜博通经术,是当时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他认为人间一切现象都是偶然发生,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存在于期间。他也认为:人的肉体与灵魂合一,所以,人的形体一旦死亡,灵魂也随之散佚,范缜提出这种《神灭论》来攻击佛教。
这个问题激起当时思想界的争辩,梁武帝及许多朝臣所主张的《神不灭论》终获胜利,使佛教更易于为中国文化人士所接纳。
四、民族文化方面
佛教源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自然会引起华人是否应该信仰外来宗教的问题。南北朝时期,顾欢的《夷夏论》可以作为这项争论的代表。
顾欢认为道、佛同源,但因中国与印度社会不同,所以,应取中国之道而弃外夷之佛。这种理论引起佛门人士的反驳,他们指出儒、道二家以治世为本,佛教以出家为宗,两者本不同源;他们又倡贵夷贱华之论,认为汉末社会风气浇薄,学术不彰,佛教却可以拯救中国。
五、调和与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信仰广为流布之后,虽然在以上所说的各个层面中,都和中国文化传统有所冲突,因而激起双方人士的辩论;但是,在不断的论难辨疑之中,双方人士相互谅解,佛教与中国文化也走向调和与融合。佛教接受中国文化的洗礼,而成为中国化的信仰;而中国文化也注入了新的血液,拓展了思想的新领域。在佛教与中国文化调和的过程中,早期比较著名的人物有牟子。牟子生于东汉末年,著有理惑论,推尊佛法,但也兼研道家。他的书兼取佛老思想,已开玄学与佛学交融之先河。宋代理学家虽然常批评佛教人士以性为空,但是佛教对理学思想影响很大。例如唐代李翱所撰的复性书就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许多宋代理学家更是有取于佛教。明末有些高僧提倡《三教调和论》,认为儒、释、道三者本质相同,理论互通。这种《三教调和论》的形成与发展,使佛教与中国文化在思想层次上更加融为一体。佛教传到中国,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调融,终于汇入中国文化的巨流,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原标题:中国佛教与洛阳白马寺清凉台)
来源:佛教导航 作者: 谢顺兵
责任编辑:佚名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下一条:武则天立升仙太子之碑上一条:中国第一古刹——洛阳白马寺佛缘
相关信息
没有记录!
著名人物
没有记录!
精彩展示
没有记录!
评论区
友情链接
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