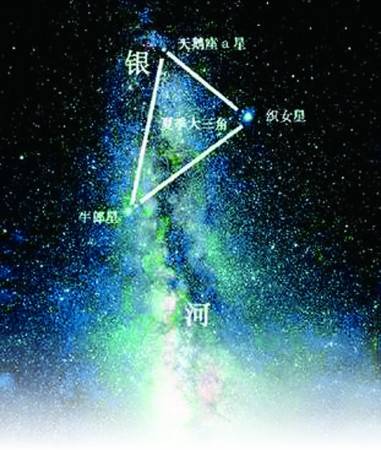-
没有记录!
- 1、获嘉同盟山与周武王伐纣
- 2、天下第一塔——河南开封铁塔
- 3、江姓探源访正阳
- 4、申姓起源
- 5、樊姓由来与济源
- 6、虎头帽虎头鞋里藏满了故事
- 7、吴姓来源
- 8、博爱皇甫姓的来历
最后的陈氏祠堂
2014/7/18 16:41:20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福州市乌龙江畔,城南城门镇的胪雷村,这座拥有七百多年历史的村落,在当地算是比较富裕的村庄。胪雷全村皆陈姓。始祖陈国初宋末时期,为了躲避战乱从福州东门易俗里徙居胪峰山内,据《福州百科全书》记载:“因村在胪峰内,简称胪内,方言谐音为今名。”
胪雷村曾走出无数知名“乡贤”,明清两代秀才、举人、进士者几十人,近代也是人才辈出,近现代最著名者有两个:国民党一级海军上将陈绍宽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
从胪雷村走到台湾的名人也举不胜举,协助梅贻琦在台创办并继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陈可忠;1945年被派往台湾接受日本投降的台北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后任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陈丞城;1981年从台湾去美国在洛杉矶创办《国际日报》的陈韬。
即便当今,该村里也出了很多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人才,更是著名的侨乡,旅外华侨遍布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陈景润是二十五世御房二支,1991年回到胪雷村省亲,也最先进入该祠堂拜祖,他的故事一直都是陈氏族人的骄傲资本。
只是,在近年来福州大拆大建的城镇化运动当中,胪雷这些显赫的村史已经失去了它的载体。
在修建福州南站时,虽然陈绍宽故居艰难地被保留了下来,目前却只是一栋空荡荡、没有任何灵魂和内容的建筑;陈景润故居却未能幸免于难,当地政府没任何通知,迅速将其拆了。
曾经绿树掩映的秀丽乡村风貌荡然无存,那些富有闽中水乡的景色变成了记忆和乡愁,祠堂、老屋、河涌、榕树、码头……那个传统意义上奉行耕读传家、聚族而居的村庄已经消失了,村民们纷纷住进了现代社区,散居各地,“胪雷村”也只剩下一个行政定义。
胪雷村只残留了着一栋占地约四亩的祠堂,它在空旷的工地中显得格外孤独,这座承载着家族悠久历史的祠堂,被大规模拆迁留下的断壁残垣围困着。
此前在拆迁胪雷村时,福州市当地政府反复承诺不拆祠堂,但就在今年5月,部分村民才获知,祠堂也面临随时被拆迁的危险。事实上,早在2013年11月,福州本土的房地产公司——阳光城集团就以39.1亿元竞得福州火车南站附近300亩地,这其中就包括陈氏祠堂。
拆迁的爪牙开始伸入这个村庄的最后精神领地。“祠堂是村里的灵魂,祖祖辈辈传下来,历代祖先牌位都在里面。以前拆我们的私宅倒好说,但现在政府又要拆掉祠堂,我们肯定不会答应。”胪雷村老人会会长陈秀光说。
曾经星散福州各地的村民开始重新集结,准备以合力保卫祠堂,保护他们最后的乡愁。
回不去的村庄
闽江可以称为福建人的母亲河,发源于闽西北山区,流经闽侯侯官处便分为两支:一支称乌龙江;另一支仍叫闽江,穿城而过。在闽江将要入海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江心岛,福州人称之为“南台岛”,而在“南台岛”的东南端,就是号称为“福州人才村”的胪雷村。
胪雷村的陈氏家族是闽中望族。陈景润被称为“胪雷之子”。在陈氏宗祠中庭,气宇轩然,依次悬挂着三块大匾,第一块上书:陈氏定理。那是褒扬陈景润的。第二块上书:教育部长。那是纪念民国时期的教育部长、化学博士陈可忠先生的。第三块上书:海军上将,陈绍宽。这三位陈氏后人给胪雷村增添了骄傲的资本。
作为从胪雷走出的教科书级“偶像”,陈景润的出身不差,他的大伯父曾任中国邮政总局考绩处处长。二伯父是中高级邮政职员,曾任福建省邮政视察室主任。他的父亲陈元俊,职位最小,只担任一个三等邮政局的局长,收入并不丰厚,家境状况并不是太好。
陈景润的父亲并不住胪雷,而是住在福州南台。不过,按照目前的资料可知,陈景润是在1933年5月22日出生于胪雷村。少年时代的陈景润,是常去故乡胪雷的。在陈景润的堂兄陈栾光眼里,他除了读书,似乎“不太爱说话,也不怎么喜欢体育运动,就是特别喜欢看书,当然也会玩一些躲猫猫的游戏”。
原先的陈景润纪念馆在天马山上,是其小学母校的校友们捐资20多万元建造的,已因福厦铁路建设被拆除,纪念馆里的文物如今存放在陈氏祠堂里。陈景润的祖宅,在村里中街附近,已有100多年历史。
2009年,福建省重点工程——福州火车南站大力开建,拆迁涉及胪雷村。按照政府当时的规划,陈景润故居将会和陈氏宗亲祠堂、陈绍宽故居择址按照原貌重建。
《福州晚报》当时报道说,“对于火车南站建设工程,陈景润的亲人很支持,同时他们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妥善保管好文物材料”。
但随后拆迁工作波折重重。在当地政府没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故居被迅速拆了,陈景润家人为此耿耿于怀。陈景润堂兄陈栾光说,陈家本想通过官司“讨个说法”,去法院起诉,但当地法院一直迟迟不开庭。
因为福州南站的建设,胪雷村曾经面临全村拆迁,村民几百上千人集结起来捍卫权益,迫使政府做出了适当的妥协。
现在,废墟中的陈氏祠堂依旧保持着往日的风貌,这让陈氏族人略感安慰。在祠堂飞檐翘角、耸峙壁立的青砖大墙前,端坐着一对石狮,昂然雄踞。抬头望,门墙顶部的青石上镂刻着泥塑浮雕,彩绘着历史典故,人物栩栩如生。
祠堂正面直书日本明治大学博士陈昌瑞先生题写的“胪峰陈氏祠堂”,显著位置摆放着陈氏家族的名人先贤的牌匾,他们代表了这个家族的荣耀。
祠堂的隐喻
“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师梁鸿在《中国在梁庄》写的这段话,形象地比喻了中国乡村的价值和意义。而祠堂,在其中是一个村庄的灵魂所在。
陈氏祠堂经历几次修缮,1947年由陈绍宽亲自主持修缮,名列福州众多宗祠之首。改革开放后,由海外宗亲再度集资修缮。故此,祠堂充当了和海外华侨联系的纽带,但凡村里组织祭奠先祖的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陈氏后人都会不远万里奔赴至此,寻根叩祖。
陈绍宽是陈氏祠堂起到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没有常年住在胪雷村,所以村里面跟陈景润有过交道的人并不多,更多的是一种价值层面的认同。而对于胪雷村真正产生影响力的还是陈绍宽。
2009年9月16日,在全国首映的电影《建国大业》中,著名影星李连杰扮演的那个角色就来自福州的胪雷村,他叫陈绍宽,民国知名的海军上将,胪雷人的行为范本和“精神偶像”。
“我认为胪雷村之所以出了那么多名人,这和它的价值观和文化生态是分不开的。”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曹敏华说。作为一位历史学研究者,陈绍宽军事思想是他的研究课题之一,他发现这位名将的人生成就的重要精神资源来自家乡。
陈绍宽的父亲陈兆雄共有六个兄弟,他是老大,他和最小的弟弟陈兆汉(萨镇冰的女婿)曾投身于清末北洋海军,常年在外。他留给陈绍宽的人格教育就是“孝悌、忠君、义气”六个字,这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陈绍宽拥有极强的语言天赋。在格致书院读书时,他就在很短时间内熟练地掌握了英、法、德、西班牙等几国语言,这使得他终生受益。在格致书院读了两年后,他又被推荐到了江南水师学堂,从此开始了他的海洋军旅生涯。
“陈绍宽对我们胪雷人影响最大了。”年逾六十的胪雷村民陈康渠说,他小时候曾在陈绍宽的大宅院内读过书,正值这位民国将领解甲归田之际。
“我们家的大宅院先盖,后来陈绍宽回到村里后也要修房子,我爷爷就给了他一块地,就在我们大院的前面,距离只有3米。原来我们院子是能看见山水的,但是他们家房子一修起来的话,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把我们家的风水给抢了。你看他想得有多细,他后面有堵墙正对着我们家的正门,为了不挡住风水,他在墙上画了一大幅的油画,有山水、森林、河流、桥梁……等于说我们家一开门就能看见‘山水’了,这是我后期发现的,后期知道的,人家细到这种程度,不服不行。”陈康渠说。
当时胪雷陈氏族人都十分团结,虽然偶尔邻里之间会有些矛盾,但因为都念在一个家族的情份上,再大的矛盾最后都能迅速化解。在化解家族矛盾当中,祠堂就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乡村社会结构当中,祠堂就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村子每年至少有一次祭祖仪式,所有陈氏家族的人都会在清明节时去祭祖,场面非常大,构成了很多胪雷人童年时代一年中最热闹的记忆、最壮观的场面。这样带有明显宗法色彩的祭祀活动,实际上提供了一个乡村社会非常综合的公共空间。
陈绍宽也意识到了祠堂作为家族精神纽带的作用,所以他返回胪雷村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缮祠堂,他本人担任董事长,陈康渠的叔公陈立卿担任副董事长。
在1949年以后,祠堂在乡村社会实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越来越低,祠堂也渐渐成为一种隐形的存在。
那个时期胪雷村的气氛已经有所变化,不再像此前那么平和,而是充满了某种骚动和不安,阶级斗争的味道已经吹进了这座村庄。
陈康渠记得,胪雷村的撕裂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反五反、无产阶级专政,一轮轮的运动将原本团结的村庄变得四分五裂,中国乡村的传统结构和文化全部被破坏了。
“人和人之间关系尔虞我诈,甚至为了果腹,不饿肚子,一个地瓜都可以打起来,要命地跟你拼搏,我看几代的亲戚、乡亲、兄弟之间为此打架结怨的多得是,为此产生世仇都有,到现在为止有些都还没有完全消除。在那个时期,我想每个乡村都是这样。”陈康渠说。
被拆掉的精神
改革开放后,胪雷村脆弱的危险的人际关系才开始修复。作为中国传统家族精神和文化纽带,祠堂在北方地区几已消失殆尽,但在福建地区却得以存留。
传统的社会秩序开始回归。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陈氏祠堂每年都会为村里老人庆祝拗九节而在祠堂举办的“千叟宴”,该传统已经坚持了32年。“千叟宴”场面极其壮观,祠堂门外支起了七八口直径1米的大锅,百名厨师齐刷刷手拿铁勺,左右开弓,为几千名老人炒菜做饭,200张圆桌摆满了祠堂的各个角落。
戏台也是记忆中的重要部分,每年都有数场闽剧在此上演,最辉煌时,每月戏班都会带着鼓、钹,到这个舞台表演那些讲述爱情、背叛、英雄和王朝的故事,这个由锣鼓、丝竹和演员唱腔组成的乡村记忆。除了本村人,附近也有村民前来观赏。站得到处都是人。
但陈康渠很快发现,好景不长,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氛围,大家只有一个目标,挣钱。再加上胪雷村本身又位处城乡接合部,所以再也无法恢复以前的平静了。
中国社会巨变在胪雷村得以投射,村里的风气也大不如前。陈康渠感觉最明显的是:“从九十年代开始,因为腐败太多,村民和政府间的关系变得有些复杂。”当然也存在其他原因,包括宗族和派系,让胪雷人不再像此前那么团结了。
2009年,经过几轮的大拆大建,这个历史文化名村被夷为平地,村民四处散居,元气大伤。“我们现在所说的乡愁,全都拆没了。”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刘泓说。
最大改变来自传统的乡村结构,胪雷村年轻一代已经很少在庞大家族氛围中长大,祠堂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年轻人的宗族意识开始淡泊了。更现实的是,年轻人都忙着挣钱,无暇顾及村务,昔日团结的村庄变成一片散沙。
“记忆中的童年没有了。”陈少辉呆立在陈氏祠堂前,说话声音低沉,走路时也尽量蹑手蹑脚,生怕惊扰了那些摆设在祠堂里的先祖。端午节时,他在北京念书的儿子回来,他特意带着儿子来到祠堂。
“拆迁会改变传统的聚族而居,这会造成下一代可能越来越淡泊。那天我并不说很多,我就注意我儿子的行为,我去观察他,问他看了什么感觉?他说没太大感觉,因为他小时候不在胪雷长大,他只知道自己是胪雷人,胪雷是个很大的村,祠堂很大,但更深层次的东西并不多。以后再下去,可能后代对宗族慢慢更淡,如果这些村落彻底地拆掉,我想将会更坏。”陈少辉说。
尽管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居住在城里,但在陈少辉看来,所谓城里依然会充满了不确定性,他最直接的依据是;中国的超大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宜居,生活在城里的人,已经陷入到一种精神失落中,他本人已有体会。更让人难过的是,曾经留存着丰厚历史人文价值的村落被快速地消灭。
2014年4月15日,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教授一行数人,调研考察陈绍宽故居和其主持修建的胪雷陈氏祠堂。眼前的一切让几位学者“十分难受”,胪雷村已成一片废墟。学者的到来,让陈氏祠堂的命运出现一丝转机。
4月18日,学者们鉴于陈氏祠堂历史悠久,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力,于是将村民诉求形成文字,报送省委省政府领导。此举引起了相关高层领导的重视,暂时将祠堂保留了下来。
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认为,尽管中国乡村早期从传统思维到现在文明的转型过程中间,还没有像现代社会制度化、组织化的合作,但它还是用很原始的乡村理念形成了一种互助情怀,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交流,这种东西说实在话是乡村里面独特的,没法代替的。还有乡村里面很重要一种品质,就是对读书人的尊重,这是骨子里面存在的。
“今天,是不是开奔驰、宝马,带几个小老婆回来,这成为了衣锦还乡的标准?所有价值用金钱来衡量的,不是学问,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精英,而是钱,这把社会风气搞坏掉了。如果换成今天的陈绍宽荣归故里,那又将是怎样的场景?这可能是我们探讨胪雷村价值意义所在。”王利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