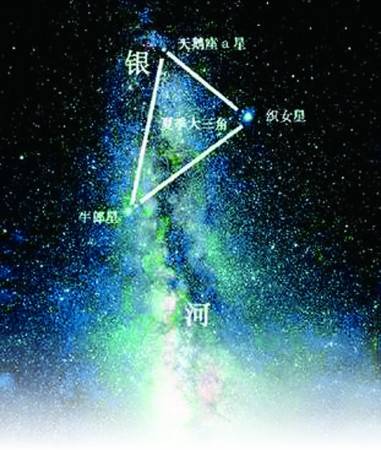精彩推荐
热点关注
- 1、钧瓷发展经历的几个重要阶段
- 2、***凤凰台 一座新城的崛起
- 3、比赛竞技显风采,象棋文化得发扬
- 4、钧窑瓷器的价值
- 5、王莽赶刘秀在鲁山留下趣名趣事
- 6、金水河:繁华穿城而过
- 7、商丘古城里的“闹龙街”
- 8、相思树
专题推荐
-
没有记录!
热点排行
- 1、钧瓷发展经历的几个重要阶段
- 2、***凤凰台 一座新城的崛起
- 3、比赛竞技显风采,象棋文化得发扬
- 4、钧窑瓷器的价值
- 5、王莽赶刘秀在鲁山留下趣名趣事
- 6、金水河:繁华穿城而过
- 7、商丘古城里的“闹龙街”
- 8、相思树
“大哉嵩山·女皇封禅篇”系列之四
2013/6/21 10:04:44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封禅是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方士“策划”的一种具有原始宗教性质的祭祀典礼,它映射着战乱频仍的年代百姓渴望天下一统的诉求。
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后,封禅与受命改制“打通”,被发展成“一种革命受命的学说”——自秦至宋千余年间,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宋真宗等七位帝王先后“承天受命”,举行过封禅大典。
秦始皇封禅是新兴王朝革命受命,汉高帝不封禅而却由汉武帝封天禅地“承天受命”,就毫无道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新情况呢?
汉与秦政治架构不同,秦实行的是郡县制,汉又回复到周的分封制:“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巫)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中央与地方诸侯各自祭祀神灵,这也许是秦亡汉兴,封禅没被“顶”出水面的一个原因。
与高帝、文景相较,“今天子(汉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史记·封禅书》写到汉武帝,第一句话就定下调调。
司马迁看到的,方士也会看到——于是,一场方士与汉武帝互动的寻仙闹剧就此上演。方士李少君甚得武帝信任,他蛊惑武帝,认为只有寻仙与封禅“双璧合一”,才能求得不死:“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也。”
李少君的理论构建无疑是相当先进的——从当时冶金技术的最高成就入手,先益寿而后再寻仙、封禅,就能够求得不死,且还有“案例”的榜样——那就是黄帝升仙的传说。李少君的理论,也回答了秦始皇封禅为何不能成仙的历史疑问,那就是他没在正确地通向仙境的道路上“运行”。
武帝即位的第十九个年头,在长安祭祀时偶然“获一角兽”。这个怪物,被有司称为“上帝报享,锡(赐)一角兽,盖(麒)麟云”。天降麒麟,封禅大门徐徐开启,“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之后,拥坐北岳恒山的常山王因为犯事,也被武帝收回封地,将常山改为一郡。这样,经过文、景二帝及武帝的“操作”,“五岳皆在天子之邦(郡)”。
武帝封禅,破除“承天受命”之说,司马迁都能够自圆其说。到东汉班固,他将皇帝总是对的与汉武帝盛世相挂钩,找到了答案,他的《白虎通》曰:“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唐代张说把封禅大典更前推一步:除易姓而王之外,又加上个“四海升平”。也就是说,虽然新王朝建立但还是必须等到坐稳天下后,才具备封禅的基本资格。汉武帝、唐高宗的封禅均可如此理解,而秦始皇、武则天以革命封禅,光武帝、唐玄宗以复辟封禅,也不违背易姓受命、功成封禅之本。
但宋真宗的天书封禅运动搞得有些过了头,尽管宋人很少直接炮轰他的封禅,却再也不愿发展封禅之说,甚至消解封禅了。在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宋儒试图从根本上瓦解被历史视为盛世大典的封禅大礼的政治文化意义。范祖禹评议封禅曰:“实自秦始,古无有也。且三代不封禅而王,秦封禅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为太平盛事,亦已谬矣……终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禅为非,以韩愈之贤,犹劝宪宗,则其余无足怪也。”叶适直言:“封禅最无据……至秦始封禅,而汉武因之,皆用方士之说,虚引黄帝而推于神仙变诈,是以淫祀渎天也。”胡寅亦云:“汉唐以来……世无达理大儒稽古正言以祛群惑,遂使有天下者于无事时肆其侈心,千乘万骑,巡狩费侈,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当代,贻讥后来。”胡寅的话,似乎话里有话。
宋儒对封禅的批判,让元、明、清帝王彻底看清这一神圣的盛世大典,不过是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衣”——天子再也不想光着屁股,让天下百姓看他们的裸体了。
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把汉武帝封禅泰山推向圣坛的,是他的裔孙、光武帝刘秀在封禅之举上的太过自谦。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已经是光武帝登基的第三十个年头,天下升平。有司奏表,请他封禅泰山,没想到光武帝这样下诏:“灾异连仍,日月薄蚀,百姓怨叹,而欲有事于太山(泰山),(污)七十二代编录(管仲言‘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以羊皮杂貂裘,何强颜耶?”
两年后,光武帝在群臣“登封告成,为民报德,百王所同”的请求声中,以人民与天帝交通的名义,“遂登太山(泰山),勒石纪号”。光武帝封禅成功,各地相继报告:“醴泉出于京师,郡国饮醴泉者,痼疾皆愈……有赤草生于水涯……甘露降。群臣上言:‘地 灵应……宜命太史撰具郡国所上。’”
对这事儿,光武帝充耳不闻,史官也很少记下这些乱七八糟的坚决支持皇帝为民封禅的瑞应。光武帝至死都很清醒,遗诏:“朕无益百姓,如孝文皇帝(西汉文帝)旧制,葬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
武帝不但有不信瑞应的裔孙,更有不信人能不死的爷爷。
高帝刘邦相信天命,但不信方士的“长生不老”,甚至对医生能治病救命,都不信:“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医曰:‘病可治。’于是高帝谩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之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如此,不治而亡。文帝继承并发展了高帝的思想,遗诏:“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理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
但夹在高帝、文景与光武之间的武帝,英武一世,到了晚年却杀人成性,求仙上瘾,沉溺在长生不老的神仙大梦里。
方士李少君出现了——皇帝喜欢,自有投其所好之人。
按司马迁的话说,李少君无妻无子,隐匿年龄与籍贯,神秘兮兮地到处游说其有返老还童之术,并利用人贪生怕死的心理诈骗金钱衣食。他“善为巧发奇中。尝从武安侯(田 )饮,坐中有九十余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少君神,数百岁人也。”以司马迁的记载结合我们现在的常识,可以断定,李少君不过是位胆大心细且有些考古常识的“诈骗高手”。
李少君不是神仙,难逃一死。但病死的李少君,却被武帝臆想为羽去不死。接着,武帝还按他的“神仙丹方”,派人东海寻仙,“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
有位叫少翁的齐鲁方士,吹嘘自己能招徕鬼神。恰逢武帝的一位心爱女人死去,得了相思病的他在少翁“幻术”的导引下,于深夜里“自帷中望见焉”。就此一招,少翁方士摇身一变,成了“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
文成将军说:“皇帝想要与神交通的话,就得把宫室打扮成神宫模样,不然神仙是不会来的。”武帝把宫殿搞成“鬼屋”,一年多后,还不见神至。文成一急,就把帛书让牛吃下,自言该牛“腹中有奇”。杀牛取书,结果被武帝识破,判为“伪书”,“诛文成将军”。
武帝既诛文成,又后悔。这时,一个叫栾大的方士找上门,对武帝说:“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他怕步文成后尘,还对武帝说:“你杀方士,那天下的方士都会闭口的!”武帝说:“文成那是误食马肝。能修神仙之方者,我爱还来不及呢!”
此时,黄河难塞,“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的说道,正好迎合武帝的心思,于是拜栾大为五利将军,“居月余,得四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数月后,“加乐通侯及天道将军印,为六印,贵震天下”。栾大吹破牛皮,说常在海上会见其师,武帝一认真,让他下海,这家伙吓得屁滚尿流,死活不下,自然遭诛。
不断的流血自然会提高方士与武帝周旋的本领。方士公孙卿对武帝说到黄帝铸鼎升仙的事儿,就让他心花怒放,于是“拜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太室(嵩山)”。“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言见仙人迹缑氏城上,有物如雉,往来城上。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假,神不来。言神事,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也。’”
武帝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若有“山呼万岁”,高兴得不得了,以为这次真要成仙了;至泰山,因儒生们都说不清封禅的礼仪,他就搬出周礼中的射牛之礼,以“射牛行事”泰山,“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其事皆禁”。下了泰山,就东至海上,企望蓬莱遇仙,结果“奉车子侯暴病”。他很可能太清楚武帝封禅泰山的装神弄鬼,遭到暗害,结果武帝对他的家人说:“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
要是子侯把武帝推下大海,说天子被神仙接走了,全天下谁会怀疑呢?
“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炼丹羽化的嵩山神仙
秦皇武帝求仙不得,驾崩而去,宣告了东海仙话的终结。
光武帝、唐高宗封禅泰山,不再东海求仙,是最好的注脚。
高宗本不相信神仙,曾说:“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
高宗能说这些话,与他的父亲李世民相信外来和尚会念经,请婆罗门岛胡僧那罗迩娑寐(或译“那罗迩婆娑”)当高级养生顾问,炼不死之药,食后一命呜呼有关。
《旧唐书》当然不能直说重如泰山的太宗死得如此轻如鸿毛。但压根儿不说吧,觉得又是史官之耻。于是,论述唐太宗之死,用了个“三段论”——
一、《太宗纪》里,不痛不痒地说了句贞观二十二年五月,“使方士那罗迩婆娑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
二、《郝处俊传》里,以郝的谏文形式说了句时人流行看法,“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秘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狄夷,法遂不行”。
三、《宪宗纪》里,一锤定音:“李藩亦谓宪宗曰,(太宗)文皇帝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
《旧唐书》虽把“太宗之死”的问题“大卸八块”,但无论如何五代史家沈 ,是对得住历史的。他这么一折腾,到宋之后,不死药在中国就基本绝迹了。当然,不死药化为养生药,害死皇帝的事儿并没有绝迹。
不死之心,人皆有之。最有条件谋求不死的人,当然是皇帝。高宗身体倍儿棒时,可嘲笑秦始皇、汉武帝乃至老父的不死梦想,但当疾病搞得他头重脚轻,目不能视,连天下都不得不委以夫人则天时,为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就不得不听信则天,寻觅不死之药了。太宗、则天无疑是唐代最伟大的男人、女人,但他们也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迷恋不死之药。她在襄助丈夫处理政务时,就积极寻求灵丹妙药,频繁接触炼丹术士。
公元668年,婆罗门僧卢迦阿逸多“受诏合长年药,高宗将饵之”,被大臣郝处俊谏阻。话说得很苛刻:你老爹死在婆罗门僧手里,是时本要问斩,怕是夷狄笑我中央大国,不了了之……话到这份上,高宗只好停服“胡药”,转向“中药”——“时高宗广令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
千古丹经王东汉魏伯阳真人炼丹嵩山,新天师道教主北魏寇谦之“尸解”嵩山升仙……嵩山自古是神仙之所,炼丹圣地,高宗命嵩山道士刘道合为其炼丹,顺理成章。
巧的是,高宗将封泰山,久雨不爽,令刘道合祈天,雨过天晴;而为封禅嵩山营造奉天宫,迁刘道合殡室,弟子开棺易衣,发现尸体唯余空皮,背有裂缝,犹如蝉蜕,“高宗闻之,恨曰:‘为我合丹,乃自服仙去矣!’”
海上神仙不遇,转而相求看得见的臣下——嵩山人间神仙。调整封禅寻仙之路,由泰山转向嵩山,无疑是一种进步:何况炼丹是那时的“高科技”,无机化学产生于斯,中医药学理论相撑于斯。
1982年,发现于嵩山之巅的武则天除罪金简,是她封禅嵩山后谋求不死的“铁证”。
在嵩山三阳宫,她吃下道士胡超为她炼成的仙丹,改元“久视”;在石淙会饮,她大宴群臣,却偷偷派胡超登上嵩山之巅,在封禅坛北侧,投下金简:“上言:大周国主武 ,好乐真道,长生神仙……”(原标题:“大哉嵩山·女皇封禅篇”系列之四)
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后,封禅与受命改制“打通”,被发展成“一种革命受命的学说”——自秦至宋千余年间,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宋真宗等七位帝王先后“承天受命”,举行过封禅大典。
秦始皇封禅是新兴王朝革命受命,汉高帝不封禅而却由汉武帝封天禅地“承天受命”,就毫无道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新情况呢?
汉与秦政治架构不同,秦实行的是郡县制,汉又回复到周的分封制:“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巫)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中央与地方诸侯各自祭祀神灵,这也许是秦亡汉兴,封禅没被“顶”出水面的一个原因。
与高帝、文景相较,“今天子(汉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史记·封禅书》写到汉武帝,第一句话就定下调调。
司马迁看到的,方士也会看到——于是,一场方士与汉武帝互动的寻仙闹剧就此上演。方士李少君甚得武帝信任,他蛊惑武帝,认为只有寻仙与封禅“双璧合一”,才能求得不死:“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也。”
李少君的理论构建无疑是相当先进的——从当时冶金技术的最高成就入手,先益寿而后再寻仙、封禅,就能够求得不死,且还有“案例”的榜样——那就是黄帝升仙的传说。李少君的理论,也回答了秦始皇封禅为何不能成仙的历史疑问,那就是他没在正确地通向仙境的道路上“运行”。
武帝即位的第十九个年头,在长安祭祀时偶然“获一角兽”。这个怪物,被有司称为“上帝报享,锡(赐)一角兽,盖(麒)麟云”。天降麒麟,封禅大门徐徐开启,“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之后,拥坐北岳恒山的常山王因为犯事,也被武帝收回封地,将常山改为一郡。这样,经过文、景二帝及武帝的“操作”,“五岳皆在天子之邦(郡)”。
武帝封禅,破除“承天受命”之说,司马迁都能够自圆其说。到东汉班固,他将皇帝总是对的与汉武帝盛世相挂钩,找到了答案,他的《白虎通》曰:“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唐代张说把封禅大典更前推一步:除易姓而王之外,又加上个“四海升平”。也就是说,虽然新王朝建立但还是必须等到坐稳天下后,才具备封禅的基本资格。汉武帝、唐高宗的封禅均可如此理解,而秦始皇、武则天以革命封禅,光武帝、唐玄宗以复辟封禅,也不违背易姓受命、功成封禅之本。
但宋真宗的天书封禅运动搞得有些过了头,尽管宋人很少直接炮轰他的封禅,却再也不愿发展封禅之说,甚至消解封禅了。在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宋儒试图从根本上瓦解被历史视为盛世大典的封禅大礼的政治文化意义。范祖禹评议封禅曰:“实自秦始,古无有也。且三代不封禅而王,秦封禅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为太平盛事,亦已谬矣……终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禅为非,以韩愈之贤,犹劝宪宗,则其余无足怪也。”叶适直言:“封禅最无据……至秦始封禅,而汉武因之,皆用方士之说,虚引黄帝而推于神仙变诈,是以淫祀渎天也。”胡寅亦云:“汉唐以来……世无达理大儒稽古正言以祛群惑,遂使有天下者于无事时肆其侈心,千乘万骑,巡狩费侈,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当代,贻讥后来。”胡寅的话,似乎话里有话。
宋儒对封禅的批判,让元、明、清帝王彻底看清这一神圣的盛世大典,不过是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衣”——天子再也不想光着屁股,让天下百姓看他们的裸体了。
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把汉武帝封禅泰山推向圣坛的,是他的裔孙、光武帝刘秀在封禅之举上的太过自谦。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已经是光武帝登基的第三十个年头,天下升平。有司奏表,请他封禅泰山,没想到光武帝这样下诏:“灾异连仍,日月薄蚀,百姓怨叹,而欲有事于太山(泰山),(污)七十二代编录(管仲言‘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以羊皮杂貂裘,何强颜耶?”
两年后,光武帝在群臣“登封告成,为民报德,百王所同”的请求声中,以人民与天帝交通的名义,“遂登太山(泰山),勒石纪号”。光武帝封禅成功,各地相继报告:“醴泉出于京师,郡国饮醴泉者,痼疾皆愈……有赤草生于水涯……甘露降。群臣上言:‘地 灵应……宜命太史撰具郡国所上。’”
对这事儿,光武帝充耳不闻,史官也很少记下这些乱七八糟的坚决支持皇帝为民封禅的瑞应。光武帝至死都很清醒,遗诏:“朕无益百姓,如孝文皇帝(西汉文帝)旧制,葬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
武帝不但有不信瑞应的裔孙,更有不信人能不死的爷爷。
高帝刘邦相信天命,但不信方士的“长生不老”,甚至对医生能治病救命,都不信:“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医曰:‘病可治。’于是高帝谩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之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如此,不治而亡。文帝继承并发展了高帝的思想,遗诏:“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理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
但夹在高帝、文景与光武之间的武帝,英武一世,到了晚年却杀人成性,求仙上瘾,沉溺在长生不老的神仙大梦里。
方士李少君出现了——皇帝喜欢,自有投其所好之人。
按司马迁的话说,李少君无妻无子,隐匿年龄与籍贯,神秘兮兮地到处游说其有返老还童之术,并利用人贪生怕死的心理诈骗金钱衣食。他“善为巧发奇中。尝从武安侯(田 )饮,坐中有九十余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少君神,数百岁人也。”以司马迁的记载结合我们现在的常识,可以断定,李少君不过是位胆大心细且有些考古常识的“诈骗高手”。
李少君不是神仙,难逃一死。但病死的李少君,却被武帝臆想为羽去不死。接着,武帝还按他的“神仙丹方”,派人东海寻仙,“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
有位叫少翁的齐鲁方士,吹嘘自己能招徕鬼神。恰逢武帝的一位心爱女人死去,得了相思病的他在少翁“幻术”的导引下,于深夜里“自帷中望见焉”。就此一招,少翁方士摇身一变,成了“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
文成将军说:“皇帝想要与神交通的话,就得把宫室打扮成神宫模样,不然神仙是不会来的。”武帝把宫殿搞成“鬼屋”,一年多后,还不见神至。文成一急,就把帛书让牛吃下,自言该牛“腹中有奇”。杀牛取书,结果被武帝识破,判为“伪书”,“诛文成将军”。
武帝既诛文成,又后悔。这时,一个叫栾大的方士找上门,对武帝说:“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他怕步文成后尘,还对武帝说:“你杀方士,那天下的方士都会闭口的!”武帝说:“文成那是误食马肝。能修神仙之方者,我爱还来不及呢!”
此时,黄河难塞,“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的说道,正好迎合武帝的心思,于是拜栾大为五利将军,“居月余,得四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数月后,“加乐通侯及天道将军印,为六印,贵震天下”。栾大吹破牛皮,说常在海上会见其师,武帝一认真,让他下海,这家伙吓得屁滚尿流,死活不下,自然遭诛。
不断的流血自然会提高方士与武帝周旋的本领。方士公孙卿对武帝说到黄帝铸鼎升仙的事儿,就让他心花怒放,于是“拜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太室(嵩山)”。“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言见仙人迹缑氏城上,有物如雉,往来城上。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假,神不来。言神事,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也。’”
武帝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若有“山呼万岁”,高兴得不得了,以为这次真要成仙了;至泰山,因儒生们都说不清封禅的礼仪,他就搬出周礼中的射牛之礼,以“射牛行事”泰山,“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其事皆禁”。下了泰山,就东至海上,企望蓬莱遇仙,结果“奉车子侯暴病”。他很可能太清楚武帝封禅泰山的装神弄鬼,遭到暗害,结果武帝对他的家人说:“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
要是子侯把武帝推下大海,说天子被神仙接走了,全天下谁会怀疑呢?
“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炼丹羽化的嵩山神仙
秦皇武帝求仙不得,驾崩而去,宣告了东海仙话的终结。
光武帝、唐高宗封禅泰山,不再东海求仙,是最好的注脚。
高宗本不相信神仙,曾说:“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
高宗能说这些话,与他的父亲李世民相信外来和尚会念经,请婆罗门岛胡僧那罗迩娑寐(或译“那罗迩婆娑”)当高级养生顾问,炼不死之药,食后一命呜呼有关。
《旧唐书》当然不能直说重如泰山的太宗死得如此轻如鸿毛。但压根儿不说吧,觉得又是史官之耻。于是,论述唐太宗之死,用了个“三段论”——
一、《太宗纪》里,不痛不痒地说了句贞观二十二年五月,“使方士那罗迩婆娑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
二、《郝处俊传》里,以郝的谏文形式说了句时人流行看法,“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秘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狄夷,法遂不行”。
三、《宪宗纪》里,一锤定音:“李藩亦谓宪宗曰,(太宗)文皇帝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
《旧唐书》虽把“太宗之死”的问题“大卸八块”,但无论如何五代史家沈 ,是对得住历史的。他这么一折腾,到宋之后,不死药在中国就基本绝迹了。当然,不死药化为养生药,害死皇帝的事儿并没有绝迹。
不死之心,人皆有之。最有条件谋求不死的人,当然是皇帝。高宗身体倍儿棒时,可嘲笑秦始皇、汉武帝乃至老父的不死梦想,但当疾病搞得他头重脚轻,目不能视,连天下都不得不委以夫人则天时,为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就不得不听信则天,寻觅不死之药了。太宗、则天无疑是唐代最伟大的男人、女人,但他们也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迷恋不死之药。她在襄助丈夫处理政务时,就积极寻求灵丹妙药,频繁接触炼丹术士。
公元668年,婆罗门僧卢迦阿逸多“受诏合长年药,高宗将饵之”,被大臣郝处俊谏阻。话说得很苛刻:你老爹死在婆罗门僧手里,是时本要问斩,怕是夷狄笑我中央大国,不了了之……话到这份上,高宗只好停服“胡药”,转向“中药”——“时高宗广令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
千古丹经王东汉魏伯阳真人炼丹嵩山,新天师道教主北魏寇谦之“尸解”嵩山升仙……嵩山自古是神仙之所,炼丹圣地,高宗命嵩山道士刘道合为其炼丹,顺理成章。
巧的是,高宗将封泰山,久雨不爽,令刘道合祈天,雨过天晴;而为封禅嵩山营造奉天宫,迁刘道合殡室,弟子开棺易衣,发现尸体唯余空皮,背有裂缝,犹如蝉蜕,“高宗闻之,恨曰:‘为我合丹,乃自服仙去矣!’”
海上神仙不遇,转而相求看得见的臣下——嵩山人间神仙。调整封禅寻仙之路,由泰山转向嵩山,无疑是一种进步:何况炼丹是那时的“高科技”,无机化学产生于斯,中医药学理论相撑于斯。
1982年,发现于嵩山之巅的武则天除罪金简,是她封禅嵩山后谋求不死的“铁证”。
在嵩山三阳宫,她吃下道士胡超为她炼成的仙丹,改元“久视”;在石淙会饮,她大宴群臣,却偷偷派胡超登上嵩山之巅,在封禅坛北侧,投下金简:“上言:大周国主武 ,好乐真道,长生神仙……”(原标题:“大哉嵩山·女皇封禅篇”系列之四)
责任编辑:C006文章来源:大河网 2006-11-13 作者:于茂世
相关信息
没有记录!
著名人物
没有记录!
精彩展示
没有记录!
评论区
友情链接
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