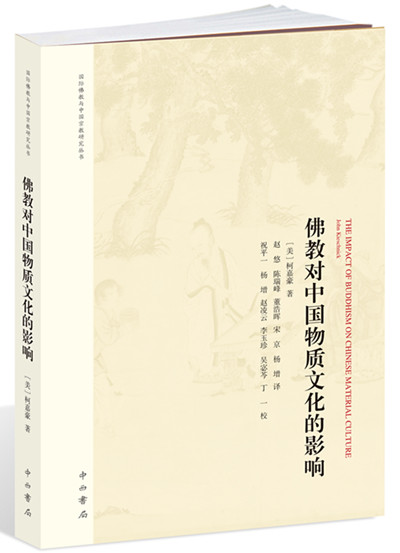精彩推荐
热点关注
专题推荐
-
没有记录!
热点排行
椅子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2015/12/7 17:26:37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最早使用椅子的是僧人
椅子从印度的寺院传到中国的寺院,在佛教典籍中有迹可循。
译于西晋的《尊上经》中已经有“绳床”(编者注:指坐具)一词,说明当时的僧人即使没有亲眼看到绳床,但至少知道印度有此物。此后,译成汉文的佛书当中亦常见此名。至于中国的僧人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绳床,唐初的高僧道宣的著作中有一则颇有价值的记载。他说:
中国(即印度)布萨有说戒堂,至时便赴此;无别所,多在讲、食两堂。理须准承,通皆席地。中国有用绳床。类多以草布地,所以有尼师坛者,皆为舒于草上。此间古者有床,大夫已上时复施安,降斯已下,亦皆席地。东晋之后,床事始盛。今寺所设,率多床座,亦得双用。然于本事行时,多有不便。
他的意思是说,当僧众举行布萨(即说戒忏悔的仪式)时,为了让众僧保持共同的法度(理须准承),一般都使用尼师坛(即方形布),坐于地上。因为从晋代以来也有僧人使用椅子(绳床),所以有时僧人同时用尼师坛与绳床,而在“本事行”(即僧人出家之前较复杂的种种仪式),两种坐法并用对执行仪式带来了一些不便。
道宣认为在中国的僧人自东晋以来使用绳床,或许是依据梁《高僧传》的记载。据《高僧传·佛图澄传》,东晋时代曾有一个水源枯竭,佛图澄“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同书《求那跋摩传》记载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求那跋摩死亡的情形时云:“既终之后,即扶坐绳床,颜貌不异,似若入定。”《高僧传》是在6世纪初叶编成,与此同时的一块造像碑上有僧人坐于椅子的图像,可能是中国图像中最早的椅子。此后,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年)的造像碑阴面与侧面,都有僧人坐椅子的描绘。
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年)的造像碑,有僧人坐椅子的描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在6世纪初中国已经有僧人使用椅子。此外,我们可以推测:在东晋,甚至更早,椅子大概已出现于中国的寺院。即使我们以最保守的年代为准(即6世纪初),汉僧使用椅子的证据还是比非佛教的相关资料要早几百年。
如同印度的僧人,中国的僧人使用椅子的最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禅坐。隋代大师智顗在描述打坐的方法时,曾建议禅者要“居一静室或空闲地,离诸喧闹,安一绳床,傍无余座。九十日为一期。结跏正坐,项脊端直;不动不摇,不萎不倚。以坐自誓,肋不拄床”。又如智顗的弟子灌顶论及“常坐三昧”时说:“居一静室,安一绳床,结跏趺坐。端直不动,誓肋不着床。”与此不同,绳床出现于僧人的传记中时,坐在其上的僧人通常不是入定,而是“入寂”。如《续高僧传·僧达传》云,僧达“一时少觉微疾,端坐绳床,口诵《波若》,形气调静,遂终于洪谷山寺”。又如《宋高僧传·辩才传》说此僧“十三年冬,现身有疾,至暮冬八日,垂诫门徒已,安坐绳床,默然归灭”。禅坐也好,静然过世也好,以下,我们会看到绳床的形象在僧团以外人士的心目中也含有恬淡无忧的意味。
在唐代的寺院,椅子也有较普通的世俗用途,比如说,僧人吃饭时也用椅子。义净在其《南海寄归内法传·食坐小床》中曾批评当时中国僧人吃饭坐椅子(“小床”)时的姿势说:
即如连坐跏趺,排膝而食。斯非本法,幸可知之。闻夫佛法初来,僧食悉皆踞坐(即垂脚而坐)。至于晋代此事方讹。自兹已后,跏坐而食。然圣教东流,年垂七百,时经十代,代有其人。梵僧既继踵来仪,汉德乃排肩受业。亦有亲行西国,目击是非。虽还告言,谁能见用?
也就是说,到了唐初,椅子在中国的寺院中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而且,那段岁月中,不断有印度比丘来到中国,也有中国的僧人去印度,但(依义净看来)中国的僧人仍然没有掌握使用椅子的正确坐姿。不论唐代僧人的姿势是否“正确”,对我们来说,最主要是义净前面的那段话,他指出从很早以来,国外的僧人就把印度坐椅子的习惯介绍到了中国寺院。
从寺院到民间
如上所述,椅子是跟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寺院。至于椅子从中国的寺院流传到一般人房屋内的漫长过程中,唐代的朝廷或许扮演了媒介的角色。
据《贞元录》,出生于南印度摩赖耶国的金刚智,准备离开印度到中国时,其国王曰:“必若去时,差使相送,兼进方物。”遂遣将军米准那奉《大般若波罗蜜多》梵夹、七宝绳床……诸物香药等,奉进唐国。至开元八年(719年)金刚智果然到达洛阳拜见玄宗,此后受到玄宗的优渥礼遇。若此文可靠,则是最早记载非僧人拥有椅子的例子。又,上所提及绘有木椅的天宝年间壁画,墓主是高元珪,高元珪是高力士之兄,因此可推论当时朝廷中应该也有人使用椅子。到了9世纪中叶,又有皇帝使用椅子的例子。日本僧圆仁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武宗“自登位已后(即841年以后),好出驾幸。四时八节之外,隔一二日便出。每行送,仰诸寺营办床席毡毯,花幕结楼,铺设碗垒台盘椅子等。一度行送,每寺破除四五百贯钱不了”。又如上所引《资治通鉴》记唐穆宗(821—824年在位)曾“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由这些蛛丝马迹看来,椅子可能是从寺院直接传到唐帝国的最高层,又从宫廷流传到民间。
不过,唐代的文献中,有关帝王资料的比重本来就很大,而明载皇帝使用椅子的记载却又很少,因此,很难证明椅子的流传与宫廷的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还有一些记载显示,除了皇帝以外,也有一些唐代士大夫,由于行政上的需要或个人的兴趣到寺院作客,因而与僧人所用的椅子有接触。
例如,圆仁曾记载,开成三年(838年)十一月“十八日相公入来寺里,礼阁上瑞像,及检校新作之像。少时,随军大夫沈牟是来云:‘相公屈和尚。’乍闻供使往登阁上,相公及监军并州郎中、郎官、判官等皆椅子上吃茶,见僧等来,皆起立,作手立礼,唱:‘且坐。’即俱坐椅子,啜茶”。又如孟郊诗《教坊歌儿》曰:“去年西京寺,众伶集讲筵。能嘶《竹枝词》,供养绳床禅。”这些都反映了世人如何接触到僧人的生活习惯。
如上所述,在三朝的《高僧传》中,绳床往往与高僧恬淡自在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这种意象对唐代的文人很有吸引力。如孟浩然《陪李侍御访聪上人禅居》诗:“欣逢柏台友,共谒聪公禅。石室无人到,绳床见虎眠。”又如白居易《爱咏诗》:“辞章讽咏成千首,心行归依向一乘。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大概就是为了追求这种悠然的理想,有些文人也在家中设置原为寺院所有的椅子。如《旧唐书· 王维传》说王维“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
到了五代,椅子与佛教的关系似乎已被遗忘了。在相传为五代作品的《韩熙载夜宴图》一画中,有椅子,也有僧人,但坐于椅子上的人不是僧人,而是贵族韩熙载。据《五代史补》,韩熙载为了过舒适的日子,拒绝为相,南唐后主李煜命令顾闳中画韩家夜宴,以揭露他放荡奢侈的生活。显然,画中的椅子显示当时韩家的富贵,与佛教中恬淡寡欲的形象毫无关系。
《韩熙载夜宴图》
南宋人庄季裕甚至认为只有僧人保留了古人的坐法。他说:“古人坐席,故以伸足为箕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为礼。盖相反矣。盖在唐朝犹未若此……唐世尚有坐席之遗风。今僧徒犹为古耳。”总之,到了宋代,椅子已经是一种日常家具。虽然寺院中的僧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仍使用椅子,但寺院以外的人已不再把椅子与佛教联系在一起。
总结以上的讨论,可知约在3到4世纪,跟随着印度寺院中的习惯,中国的僧人开始使用椅子;在盛唐到晚唐时期,有一部分居士以及与佛教有接触的人也开始使用椅子;至五代、宋初,椅子开始普遍流行于中国家庭。椅子的历程可视为佛教影响中国社会的范例,说明传到中国的佛教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信仰系统,而且同时包含了许多我们平时想不到的因素。换言之,椅子的历史显示,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漫长过程中,除了教理及仪式以外,佛教也带来了各式各样的器物及生活习俗。
日本人、韩国人为何仍席地而坐?
以上的讨论虽可以告诉我们椅子如何在中国出现、流传,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椅子成为中国文化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只要看一下日本的室内就能体会到这点。正如汉僧一样,日本的僧人也读过提及绳床的律典,也看过玄奘与义净对于印度寺院的描写。圆仁的日记显示,日本的中国留学僧也注意到中国寺院中的椅子。而从日本中古时期的绘画及正仓院的藏品中,可知当时日本僧人确实曾从中国把一些椅子带回日本。然而,椅子在日本始终不如中国兴盛。在近代西方的影响下,日本大量地引进及生产椅子,但即使现在,典型的日本家庭仍然以席子为主,而非以椅子为主。
由此看来,从席子搬上椅子并不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趋势。说椅子的出现推广了卫生习惯,并“对中华民族身体素质提高或许有益”,是“古代文明的一种进步”,是“向纯理性方向的发展”恐怕都不能成立。铺席子的家庭往往讲究干净,属于席地而坐的文明(日本、韩国、波斯等),通常觉得席地坐比坐椅子舒适。这种问题与兵器及一些其他科技的流传不同:国家为了自保会学习敌人的优势兵器;近代,眼镜从西方传到中国而很快被广泛使用,也不出人意外。但用不用椅子,与一个文化的生存没有直接的关系,用椅子是否比席地而坐方便也很难说。由此可知,由席子转变到椅子,是基于一些相当主观的文化因素,而与较客观的科技及卫生等因素似乎无关。
至于中国人之所以改用椅子的原因,我在前面提到了几个可能,如弥勒像的普及、椅子在寺院中的运用、非僧人与寺院生活的接触,以及椅子与悠然平静的人生态度的联结。不过,虽然这些因素也曾同样存在于日本和韩国,但他们并没有广泛接受椅子。显然,椅子的历史相当复杂,仍有许多待阐明之处。然而,我希望以上的讨论说明了一个较小而仍然重要的现象:中国人从低型家具发展到高型家具的过程中,椅子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佛教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文节选自[美]柯嘉豪(John Kieschnick)著, 赵悠、陈瑞峰、董浩晖、宋京、杨增 译,《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中西书局,2015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责任编辑:C006文章来源:私家历史(2015-09-30)
下一条:没有了上一条:中秋节诗词
相关信息
没有记录!
著名人物
没有记录!
精彩展示
没有记录!
评论区